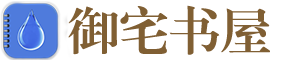温什言,回来了
作品:《偏科(H)》 一周后,温什言带着luca,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行李不多,一个二十八寸的托运箱,一个登机箱,再加一个航空猫包,luca已经四岁了,从一只巴掌大的小奶猫,长成了体重超过十斤的大姑娘,它品相独特,湛蓝的眼睛,蓬松柔软的毛发,性格却很反差,黏人,脾气不行。
温什言也怪自己,总是宠着它。
十一个小时的飞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她醒来时,飞机正在下降。
再次见到香港,她心里复杂,这座城市和她记忆中一样,拥挤,繁华。
温什言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再睁开时,飞机已经停稳了。
落地,取行李,过海关,一切顺利。
她推着行李车走出抵达大厅,香港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属于南方的气息,她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忽然有些恍惚。
四年,就这样了。
打车去会景阁的路上,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男人,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问她从哪里来。
“悉尼。”温什言回答,目光落在窗外飞逝的街景上。
“哦,留学回来啊?”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读的什么?”
“金融。”
“厉害厉害。”司机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女儿也在读大学,学的是会计,以后也想进银行工作。
温什言听着,偶尔应一声,心思却已经飘远了。
会景阁什么都没变,还和她刚来这里时一模一样,只是门口的保安换了人,是个叁十出头的年轻小伙,看见温什言推着行李过来,礼貌地上前询问:“小姐,请问找哪位业主?”
温什言摘下墨镜:“我住这里。”
保安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脚边漂亮的布偶猫和行李箱,脸上掠过一丝迟疑,但很快,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态度立刻变得恭敬:
“是温小姐?抱歉,您很久没回来了,需要帮忙吗?”
温什言略一点头:“麻烦帮我拿一下行李箱,谢谢。”
保安连忙应下,帮她拎起较重的那个箱子,引她进入大堂,刷卡,Luca在航空箱里不安地动了动。
到了地方,保安帮她将行李放在入户门外,便礼貌地告辞,温什言指纹解锁,门“嘀”一声轻响,开了。
一股类似檀香混着阳光的味道飘出来,没有预料中陈腐的尘埃气,她顿了顿,推门进去。
屋内光线昏暗,她摸索着打开灯,瞬间,暖黄的光线铺满整个开阔的客厅。
一切如旧。
深灰色的沙发,原木色的茶几,整面墙的落地窗,关着帘子,地板光洁如新,家具一尘不染,甚至连窗台上的那盆绿植都还活着,叶片翠绿,长势良好。
这是有人定期打扫,才能维持的。
luca从航空包里钻出来,先是警惕地观察了一会儿,随即像是认出了这个地方,欢快地“喵”了一声,小跑着跳到沙发上,熟练地找了个最舒服的位置,蜷缩起来。
温什言看着它,笑了笑。
她脱下鞋子,赤脚踩在地板上,冰凉的温度从脚底传来,走到落地窗前,拉开帘子,阳关下一秒落进来,温什言闭眼,感受,忽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四年了,她竟然又回到了这里。
手机在这时响起。
温什言从包里拿出来,看了眼来电显示,付一忪。
她接了。
“喂。”
那边安静了两秒,随即传来付一忪的声音,带着点咬牙切齿:
“温什言,你回香港了?”
温什言“嗯”了一声。
“好歹陪了你四年,你好狠的心,不说一声留我一个人在悉尼。”
付一忪的语气半真半假,听不出是责怪还是玩笑。
温什言转身,走到沙发边坐下,luca立刻蹭过来,把头搁在她腿上。
“我没让你陪我。”她说,声音平静。
言外之意,你该的。
电话那头,付一忪笑了。
那笑声很低,却无可奈何:
“行,你厉害。”
“还有事?”
温什言问,手指无意识地梳理着luca的毛发。
“等着。”
付一忪只说了这两个字,就挂了电话。
温什言看着暗下去的手机屏幕,挑了挑眉。
等着?
等什么?
她没多想,把手机扔到一边,起身开始收拾行李,衣服挂进衣柜,书摆上书架,洗漱用品放进卫生间,一切都做完后,她给luca倒了猫粮,换了水,然后才想起物业费的事。
杜柏司预缴了五年,算算时间,应该快到期了。
她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声音甜美的女客服,听说她是会景阁的住户,语气更加恭敬:
“您好,温小姐,这里是会景阁物业管理中心。”
“我想缴物业费。”
那边说了句“稍等”,估计是查了下资料,声音响起。
“抱歉打扰,关于您物业费的事宜,杜先生在四年前的八月份,又为您这套单位预缴了二十年的管理费及基本维护基金,您目前可以放心居住,无需担心续费问题。”
温什言听着,脸上没什么意外。
“他有留存银行卡号码吗?”
会景阁的物业费高昂,预缴如此巨额,通常户主会绑定自动扣款账户,若房子空置,多出的费用会按协议退回。
那边停顿了两叁秒,似乎是在查询或确认权限,然后回答:“有的,温小姐。”
“好。”温什言说,“把号码发到我这个手机,短信即可。”
“好的,温小姐,稍后发送。祝您生活愉快。”
电话挂断。
物业很迅速,几乎是十分钟后,一串号码发了过来。
沙发上,温什言抱着luca,手指陷进它丰厚的皮毛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顺着,猫的身体温热柔软,喉间发出满足的呼噜声,蓝眼睛半眯着,对这阔别四年的旧领地毫无芥蒂。
她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长到香港的夜晚悄然来临。
温什言手指无意识地揪住luca后颈一小撮毛,猫不满地“喵”了一声,扭动身子,温什言松开手,顺了顺那处,目光落在茶几上安静躺着的手机上。
拿起来,解锁,调出下午物业发来的那串银行卡号,数字很长,属于某个她不关心也永远不会去查的海外私人银行,她眼神平静,指尖在屏幕上点按,
输入金额:500000。
币种:港币,备注栏空着。
确认,转账。
指纹验证通过,屏幕跳出“交易成功”的提示,转瞬消失,退回冰冷的账户余额界面。
她盯着那界面看了两秒,然后把手机丢回沙发深处,机身撞在柔软的真皮上,发出一声闷响,luca被惊动,抬头疑惑地看她。
温什言站起身,赤脚踩过冰凉的地板,径直走向浴室,衬衫下摆从腰间滑出一点,随着她的动作,勾勒出名为女人味的身材曲线,她没回头。
水声很快响起,盖过了心里不该触碰的声音。
北京,长安俱乐部。
顶层包厢,兰字间。
季洛希组的局,周顺和汪英梵都在,杜柏司到得晚,推门进来时,里头正闹着,汪英梵倚在吧台边,手里晃着一杯酒,正对着坐在高脚凳上的周顺眉飞色舞:
“你是没见着,林佳宥坐上那个位置时,那几个老东西的脸,绿得跟王八盖子没模样,非嘉这摊烂账,总算是理明白了。”
他啜一口酒,咂咂嘴:
“要我说,男人就不能像你这样温柔。”
周顺只是听着,这调侃来的猝不及防,他抬脚踢了下人,季洛希躲开,狡黠的笑。
周顺不理他,手里拿着一杯酒,却没怎么喝,指尖在杯壁上慢慢划着圈,他比四年前更沉稳,或者说,更沉静了,那股子不动声色的劲头,跟周家老头一模一样。
他抬眼看了一下刚进来的杜柏司,微微颔首。
杜柏司扯了扯嘴角,刚那一幕看完全了,他脱下西装外套,随手搭在沙发背上,里面是一件黑色衬衫,领口解开了两颗,袖子挽到小臂,四年的时光在他身上凿下了更深的痕迹,肩背的线条依旧挺括,甚至因长期处于高压而更显出一种紧绷的力量感,但眉眼间的倦色是盖不住的,那不是睡一觉就能消解的乏,总之,是这样的,杜柏司的青春年气只在四年前存在过片刻。
“哟,杜总可算是赏脸了!”
季洛希从里间晃出来,手里拿着瓶刚开的红酒,他是四个人里变化最外露的,一身剪裁刁钻的银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写着“高级”两字,只是眼底那点玩世不恭的精明,倒是一点没变。
“前两年还好,这半年,想约您老人家吃顿饭,比见部长都难,周顺的面子都不好使了,今儿要不是我说我新得了…”
“少废话。”
杜柏司打断他,声音有点哑,径直走到中间沙发坐下,接过季洛希递来的酒杯,看也没看,仰头就喝了大半,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丝灼热,暂时压下了胃里的不适。
“就是,”汪英梵凑过来,一屁股坐在杜柏司旁边,胳膊搭上他肩膀,带着酒气。
“我说你,集团现在还不够你横着走?东南亚稳了,非嘉也收拾利索了,澳洲那边听说也铺开了路子,你还这么拼死拼活图什么?真当自己是铁打的?”
他凑近些,压低声音,却足够让所有人都听见,带着点男人间心照不宣的戏谑:
“回去好好睡一觉,补补元气,我看你这几年,怕是难得有几个晚上睡得比在飞机上踏实吧?”
周顺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汪英梵讪讪收回了胳膊:
“少说两句。”
他看向杜柏司。
“胃又不舒服?”
杜柏司摆摆手,没说话,只是把剩下的半杯酒也喝了,空酒杯搁在玻璃茶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他往后靠进沙发深处,闭了闭眼。
包厢里光线昏暗暧昧,灯是碎亮的,落在他垂下的眼睫上。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气味,好闻,却又不舒适,总之,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这是他们的世界,他早已习惯,甚至游刃有余,只是这一刻,疲惫感排山倒海。
季洛希又给他满上,笑着打圆场:
“行了行了,汪少也是心疼你,不说那些烦心事,今天好不容易逮着你松口气,甭想逃酒啊。”
汪英梵睨他一眼:“滚蛋!”
他不爱这个称呼,什么汪少,像在唤狗一样。
杜柏司扯了扯嘴角,算是应了。
又喝了两杯,胃里的疼痛开始抗议,他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脸上那点敷衍的笑意也挂不住了。
这几年太忙,忙到脚不沾地,清理董事会的老顽固,肃清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网,将冧圪彻底攥在手心,然后向外扩张,东南亚,澳洲,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不容半分差错,饭吃得潦草,觉睡得零碎,胃出了点问题,医生警告过几次,他没时间,也没心思认真调理,疼惯了,也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又喝了几轮,汪英梵开始讲他新看上的一个小模特,季洛希笑着调侃他品味一如既往的“接地气”,周顺偶尔搭一两句腔,话不多,但总能接在点上,杜柏司听着,偶尔应一声,大部分时间沉默。
香槟,威士忌,红酒混着下肚,酒精慢慢蒸腾上来,太阳穴一跳一跳地胀痛,胃里那点火却烧得越来越明显,带着钝钝的坠痛。
他搁下杯子,起身:“我歇会儿。”
没人拦,都知道他累到极致了。
他走到包厢另一侧靠墙的宽大沙发旁,整个人卸了力倒下去,真皮沙发冰凉,贴合着脊背,他随手抓过一个刺绣靠枕,抱在怀里,脸埋进去,这个姿势有些孩子气,与他平日冷峻的形象格格不入,但他太累了,累到懒得维持任何姿态。
周顺对侍者低声吩咐了一句。
很快,一条柔软的薄毯盖在了杜柏司身上,他动了动,没睁眼。
包厢里一时安静下来,汪英梵摸了摸鼻子,坐到吧台边,小声跟季洛希嘀咕着什么,周顺回到原位,端起自己那杯一直没怎么动的酒,慢慢喝着,目光落在虚空里,不知在想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也许有半小时。杜柏司陷在半昏半醒的困倦与胃部持续不断的隐痛之间,意识浮沉,手机在裤袋里震动起来,嗡鸣贴着大腿皮肤。
他皱了皱眉,极度不愿被打扰,但震动一遍又一遍。
他从毯子下伸出手,摸到裤带,掏出手机。
屏幕亮着冷白的光,刺得他眼睛眯了眯。
两条新消息。
一条是银行入账通知。
港币,五十万整。
汇款方账号……陌生,但归属地显示香港。
另一条,是紧随其后的账户余额变动提示。
杜柏司盯着那串数字,和那个香港的区号。
酒意,疼痛,倦怠,在这一瞬间,全杂在一起被这条消息打乱。
悉尼那边没有传来任何她回国的消息,被瞒得滴水不漏。
好,很好。
温什言,回来了。
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指腹摩挲手机屏幕,胃里猛地又是一绞,这次却不是因为病症,而是近乎痉挛的情绪,他下意识地更用力按住胃部,额角的冷汗汇聚成滴,滑落到鬓边。
电话打到另一边。
“冷晓生。”
他对着手机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刚醒的涩。
“查,人是不是在会景阁。要快。”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等待的几分钟,长得像一个世纪。
包厢里,汪英梵和季洛希似乎又开始了新的话题,声音压低了,夹杂着低笑,周顺依然安静地坐着,目光却已转向他,带着询问。
杜柏司没理会,他维持着那个略显狼狈的趴伏姿势,手里紧紧攥着手机,眼睛盯着暗下去的屏幕,所有的感官都凝聚在等待的焦灼上,胃部的疼痛反而成了提醒,提醒着他这四年的真实代价。
手机终于再次震动。
他划开。
冷晓生的信息,言简意赅:
【温小姐今日上午十点十七分落地香港赤鱲角机场。出关后搭乘车牌789出租车,沿西九龙公路至维多利亚港一带绕行约四十七分钟,最终目的地会景阁。安保人员协助提拿行李,温小姐态度客气。】
绕行维港,四十七分钟。
他闭上眼,几乎能想象出那时的场景,她坐在出租车后座,车窗外的香江景色流转,她看着,或许面无表情,心里却在冷静地计算着路线,时间,确认有无尾随,甩掉可能存在的眼线。
四年商学院,没白读,金融模型没白啃,连这点反侦察的谨慎,都无师自通了。
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