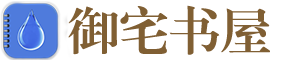第七十二章 rourouw u7.c om
作品:《盈满则亏》 春宵帐暖,暗香浮动,柳湘盈好似飘在云端,不知过了多久,腿心好像永远被插着什么。
或是唇、或是舌、手指还是阴茎……她又热又累,背后压着沉沉躯体,一阵剧烈的噗嗤声断,脖颈紧压的力道骤然减轻。
谢远岫压着柳湘盈,软掉的阴茎堵着穴口没抽出来,两人喘息交织,她后背贴着谢远岫的胸膛,似乎能听到他剧烈的心跳声。
隔着皮肉,一下一下震在她心头。
身下的女人双眼朦胧,似乎还没从不断的高潮中缓过劲,张着嘴露出软红的舌尖。
谢远岫没想,低头含住,舌头最先碰到,而后是唇,牙齿,柳湘盈张着嘴让他入了,两人唇舌都吃得水光淋漓。
谢远岫蹭着柳湘盈的脸,后颈厮磨缱绻,两人亲昵得如同窝里的两只小兽,亲密缠绵。
谢远岫抱着人又去清洗一次,收拾好两人便抱着沉沉睡去。
再睁眼,不知道是什么时辰,柳湘盈动了动指尖,身上酸痛得厉害。日光正盛,她下意识眯了眯眼睛,随后眼上盖上阴影。
她眨了眨眼睛,鸦羽似的睫毛扫过谢远岫掌心,细密的痒钻心一般,挠得人难耐。
谢远岫掰过柳湘盈的脑袋,就这么低头含住唇舌,舌头挑开双唇,勾着湿滑的唇舌舔弄交缠。
日光好景落在亲吻得发丝纠缠的二人身上,肌肤如玉,水声暧昧,谢远岫啄着肿胀的唇瓣,难舍难分。
柳湘盈被闹得痒,抬手推他,被抓住手拢在掌心,按在胸膛上。
心跳沉稳有力,柳湘盈渐渐出了神,谢远岫抓着她的手放到唇边,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今日有许多事情。”
“嗯,盈娘明白。”
谢远岫抚摸她的脸颊,说:“谢六也不得空,让他替你安排人。”
柳湘盈眼睫轻颤,望向谢远岫,许是日光偏爱她眼眸柔软得猫儿似的。
谢远岫轻叹一声,将人拢进怀里,鼻尖的味道分不清谁是谁的,只觉得异常安心。
盈娘,盈娘——
“盈娘……”
她一向是温顺可人的,或者说京畿时,温顺得万事由人只是她自保的手段。
谢远岫一直都知晓,温顺也好,冷情得固执也罢,他并不在乎。
谢远岫离开后,柳湘盈又休息了会,直到身子不怎么酸痛才起身。
柳湘盈起身收拾好自己,吃了点东西便让人吩咐马车离开,谢六已经安排好,不会有人阻拦问询。
回到铺子,忙到夜半时分,便打发后门的轿子回去,自个儿就不回去了。记住网站不丢失:vip yzw.c o m
头一晚,轿夫怕得很,死活不敢回去,柳湘盈便留人住下,如此两三日,府上静悄悄的无人来唤,才渐渐放下心,每日都回去报信。
日子久了,绪兰和况莲儿也渐渐放下心来,任谁都看得出绪兰脸上的笑容多了不少。
况莲儿笑道:“小妮子近日怎的了?莫不是好事将近,不应该呀,我这个做娘家人的都还不知道。”
绪兰指尖沾水,轻甩过去,“去!”
“我是替小姐开心。”
自从来了蓟州,几人姐妹相称,况莲儿许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一时间有些恍惚,沉默下来。
这也不怪她,着实三年前的事印象深刻,只怕是忘不掉。
“终于是结束了,”绪兰低声道,“兜兜转转也不枉费我们逃到了这儿,小姐也不必再逼着自己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不喜欢?
况莲儿看了眼绪兰,“盈娘同你说的?不喜欢谢大人。”
绪兰摇头。
况莲儿想着点破,如今的情形说不准,可若说不喜欢,柳湘盈自个儿都没法否认。
“盈娘既然没说,你便当——”况莲儿嗫嚅,索性心一横,道,“你便当她有些心思吧,真心假意总有两三分。”
“我知道。”绪兰轻声打断,“可小姐既然选择逃出来,那些喜欢就不值一提。”
“而且是谢大人来了蓟州,不是我们回京,真心假意,小姐看得清就好了。”
绪兰说完,况莲儿有些呆住,回神仰头看向紧闭的房门,脑海中有根弦忽的一颤,“盈娘今日出门了吗?”
“没有,前几晚熬得厉害,研制出些新的香,这会儿姐姐估计还在睡。”
况莲儿看了片刻,对绪兰道:“那这几日我们便多顾着点铺子,好好想想那些香料的去处。”
金贵香料都会先送去关系稍近的官宦人家,哪家都少不得。
高门富户,馨香阵阵,不少经过的人便觉着身上带香,经久不散。
不少来议事的官员近日都觉着有些奇怪,家中和谢大人府上似乎味道相似,一天下来,好像被腌入味儿了,幸而香淡,闻着倒也舒心。
经过多日磨合,谢大人也不如之前冷厉,说不上热络,但也和颜悦色许多,供上的茶水点心花样也只多不少,言语间也融洽不少。
头一次,天色还亮着,每位大人都是带着清香,面带笑容地离开的。
“谢大人近日很得人心。”
听到背后的声音,谢远岫并不意外,他喝了口茶,仿佛吞了口蜜,愈发口干舌燥。
柳湘盈心想,她才多放了三勺蜜。
谢远岫抬眼,面无表情地又喝了一口,“甚好。”
柳湘盈靠在一边,别过眼,将窗子推开些,任由晚夏的风吹进来,吹散了茶香和燥热。
谢远岫知道她还有些生气。
那次做完,两人又是一段时间没见。
她有一日晚间才回来,来不及换上身上的衣服,谢远岫闻见她身上的味道有些不同,便问是什么香,她拿出一小颗,说平时无碍,但要小心使用,不能碰水。
她一说,谢远岫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手边正好是没喝完的茶水。
那夜风轻云散,月色明亮,身下的胴体也如羊脂膏玉,更加动情紧致,穴里缴得他刚插进去就一股射意,放浪不堪。
两人见面后,柳湘盈回府的日子不多,谢远岫也随着她,只实在太久便差人去问一声,得到的结果大多不同。
今个儿去通判府上。
明儿又去了郊外,同些香料商人共话。
过了几日,院子里又多了几盆未曾见过的奇花,香味冷冽扑鼻。
据说难养得很,柳湘盈很宝贝,恨不得一天天挂在花枝上。
她盯花盯得紧,没成想第二日连花带人换了个地儿,人养在屋子里,花养在外头,一天三次有人照看。
柳湘盈没说什么,还是挂心自己花儿,枕着谢远岫的膝盖看书,得空时不时就看一眼。
知道她心里记挂着,谢远岫让人将花养在跟前,时不时就能见柳湘盈瞥了一眼又一眼,关心得容不下旁的了。
他撑着头看了片刻,手腕一折,书本严严实实挡在柳湘盈面前。
“看了许久书了,仔细眼睛疼。”谢远岫抬了抬下巴,“休息吧。”
柳湘盈翻身,轻车熟路地撑在他膝头,脸枕着自己的手臂,眼睛水润明亮,连点血丝儿都见不着。
看来这些日子休息得不错。
“三哥累了?”
谢远岫嗯了一声,“看你时不时往外看,眼睛估摸着也看得难受了,躺会儿?”
柳湘盈不置可否,按照以往,是会依着他的。
不过这个以往,也隔了三年之久。
柳湘盈抬手摸了摸谢远岫的眼皮,指尖轻压在他眉尾,“不及三哥,公务繁忙,是该多休息。”
她的手法很好,不知按压了哪处穴位,微微用力,酸胀的脑仁却得以舒缓,有些昏昏欲睡起来,朦胧间便听柳湘盈轻声道:“那三哥早些歇着,盈娘就先回去了。”
谢远岫睁眼,身子还未起,直接伸手将人拽回来,最后一点点遮掩的意思都没有,柳湘盈没忍住,在他怀里笑出声。
谢远岫半抱进怀里,箍着她,右手在她笑得发抖的后颈暗示性地揉弄,柳湘盈不在乎,笑眯眯地窝在他怀里瞧着,嚣张得很。
她拾起刚才的书举到脸边,挡住自己和谢远岫的半张脸,柳湘盈的笑声淡了,淹没在纸墨香气中。
书页翻动摩擦,后颈的手转揉为压,女人鬓发微动,嘬吸的声音很低,只能漏出些舔弄的水声,细流蜿蜒在不断移动变幻的高大山尖。
后颈的手泛起青筋,她被掐着脖子含弄,翠绿的钗子闪烁微光,闪烁在男人失神的面上,鼻息发沉。
什么花,什么书,都抛之脑后。晚夏正好,谢远岫偏爱她日光下的躯体,神情、体态,动情难制的颤抖淋漓,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那些花不仅可以做香料,还能入膳。
府中议事的官员也能得些口福,有时谢大人府上的茶点都是变着法儿的上,迎合时节又新奇得很。
谢大人府上的香也格外奇特些,在别处闻到差不多的,总感觉有什么不对。
众人也都知道谢远岫同那擅香的貌美寡妇的事儿,只是没想到二人长情,谢大人再蓟州四五月,熬过盛夏初秋,情谊都没半分变化。
除了偶尔茶店变更,寡淡无味,让人意外。不过主家坐在上座,神色自如,其他几位只好尝不出,就当他们夫妻情趣罢了。
偶尔茶点寡淡,吹毛求疵,偶尔如春风和煦,不拘一格,统统都是有的。其他大人还好,唯有通判大人,平日里总是动静大些,分外小心。
谢远岫又在蓟州待了半年之久,同行的萧世子随性惯了,当年九月就先回京,临行前给谢远岫个口信便离开了。
谢远岫待到入冬,炭火刚点起来,京畿便来信催促,还告知娄氏病重,性命垂危。
彼时谢远岫同柳湘盈刚浓情蜜意完,正值分别之际,两人面上不显,但都有些心浮气躁。
屋子里沉闷地可怕,谢远岫得知柳湘盈在通判府几年,竟然从没见过几次通判大人,都被安排着从后门离开。
柳湘盈抬眼,语意不明:“那次我好像还看见三哥了。”
当时谢远岫已经知道她在通判府,有意避让,没想到在花园处碰上,当时没多想,现在才明白,是她尽心尽力却被人一直防备着。
红墙绿瓦下腌臜事只多不少,一个兆夫人都如此,更何况其他。
谢远岫没说话,可柳湘盈知道他生气了。
气她自作自受,自讨苦吃。
谢远岫摆手,让她过来。
柳湘盈抬脚往门外走,丝毫不顾及身后冷掉的脸色。
几月的时间,两人闹脾气的次数比前面加起来都多,两人似乎都没有忍让的意思,柳湘盈更是清清楚楚地袒露出来,两人的差距、两人的关系,都该趁着此时,断得一干二净。
兆夫人之流不算什么,曾经会贬低她,现在看在谢远岫的关系,也不会对她怎么样。将来谢远岫离开,她就将铺子作为绪兰的嫁妆,让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柳湘盈想得通谢远岫为何生气,但她没有和好的打算。
谢远岫离开在即,蓟州官员相送,送来的东西满满当当,堆了半间屋子。
柳湘盈也送了,在礼单的最后一行——一只香包,一条佛珠手串。
两样东西搁在桌上,干净如昔。
谢远岫看着这两样东西,忽的开口道:“谢六,去找个人。”
谢远岫一走,柳湘盈的地位瞬间尴尬不少,她搬离府上,干脆闭门不出,专心休息。
两人半路夫妻,在旁人眼里,这貌美寡妇是连外室都算不上,顶多是个意趣。
没人撑腰,以前的营生是没法做,没人再会和之前一样,让柳湘盈伺候自己,这生意自然也是偶尔光顾。
说不上一落千丈,但冷清许多。
柳湘盈却面色如常,看不出丝毫担心,她想到过如今的情境,好在给绪兰的已经备好,况莲儿也有了身孕,在家安胎,她留够了钱财,也不用让她二人担心,一个人再冷清也冷清不到哪去。
再过几日,谢远岫也会离开,离开蓟州,回到京畿,回到谢府的高门大户中,天各一方。
“盈娘。”
柳湘盈眨了眨眼,眼角湿润,她想得入神,疑心是自己听错了,仍愣愣的。
直到被一双手自背后拥住,柳湘盈低头看着熟悉修长的手盖在自己小腹,她目光微动,身子仍僵着。
耳边呼吸发沉,急促地喷在她颈侧。温度和背后的胸膛一样,炙热得紧贴着她,由不得她抗拒似的,全部揽住。
柳湘盈冷着心肠,“谢大人,你做什么?”
谢远岫不理会她的冷言冷语,将人往屋里带。
一进屋,轻车熟路地找来印泥和纸笔,抓着柳湘盈的手,拥着她站在桌边。
他抱着她,却也是禁锢着柳湘盈。
笔尖迟迟未落,两只手紧紧握住笔杆,像是在各自抵抗,实则她的手被握得生疼,毫无反抗余地。
“谢远岫,”柳湘盈指尖都没法动,双腿也被夹着,只能出声提醒,“这是要入官府的。”
“我现在是个寡妇。”
“我知道。”
红色的婚书,红纸在昏暗的烛光下依旧异常鲜艳。
柳湘盈没想到谢远岫拿来这个。
嘉礼初成,良缘遂缔。
永结鸾俦,共盟鸳蝶。
柳湘盈看着这几个字,像是遥不可及的梦,她红了眼睛,整只手臂挣扎发颤,说:“谢远岫,我不愿意。”
“我知道。”谢远岫手腕用力,强硬地带着柳湘盈缓缓落笔,“但你我本是夫妻。”
她挣扎得厉害。
谢远岫只能整个人压上去,动作间衣料滑动,她看见谢远岫腕子上熟悉的手串。
红纸上字迹颤抖,一笔下来粗细不一。
谢远岫箍着她的腰,毫不在意字迹粗糙,一边写,一边说:“礼成后,你不必担心,我会打点好一切。在蓟州没有人会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过去。在京畿,柳府、谢府都不会有人来寻你。”
柳湘盈靠着他的胸膛,呼吸剧烈。急促的声音像是从谢远岫身体里发出来,心口那处像是漏了风,又冷又黑。
谢远岫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同她一样。不想要弃如敝履,想要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放手。
“以后,你便是蓟州人氏,经营着香料铺子,有自己的香料生意。京畿,你想去便去,不去就不去,即使回去了也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
最后一笔落下,谢远岫下巴蹭着她的脸颊,亲昵地贴着她耳语,“从此再没有柳湘盈,只有蓟州盈娘,谢远岫的发妻。”
谢远岫回到京畿后,只来得及见娄氏最后一面。
他打理好一切将谢府托付给薛道宜,做主让小满认薛道宜为母亲。
三年后,丁忧结束。
蓟州谢氏悄然兴起,货通南北,官达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