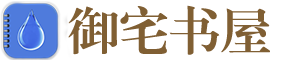第106章
作品:《美人假少爷靠直播鉴宝爆火[古穿今]》 他忽略,又重复了:“听到没。”
余晏白了他一眼,“遵命,领导。”
“这才乖。”席澍满意一笑。
临安机场规模挺大,就算两人走vip速通通道,也还是折腾了半小时才坐上安排好的车。
说来这还是余晏第一次来母亲的故乡,跟母亲说的一样,秋天时仍连风中都带着清新草木的香味,道路两边是林立的绿树,似一把紧密密的大伞。
就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破坏了他的想象,毕竟母亲描绘是青瓦白墙的江南山水。
他不满的时候,鼻头会微微一耸,席澍一下就捕捉到了:“怎么了。”
余晏说:“怎么都是棒槌一样戳着的大楼,临安老式的建筑呢。”
席澍霎时就反应过来他在不高兴些什么:“临安是新一线城市,这块是新科技板块,旅游景点附近还是很多老式建筑的,等我们见完余枫,一起去逛逛。”
“好。”
余晏点完头之后不说话了,支倚在车窗旁,浑身的血液仿佛都静止在血管里,而后又疯狂倒灌到脑袋上。
席澍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但面对余晏总是很细致的,他把手搭在余晏的手上,手指钻进指缝,紧紧扣住。
余晏眼神仍旧虚浮在空中,只不过手上也很用力地回握了过去。席澍手指极其有力,余晏能清晰感受到他大拇指上的粗茧,痒痒的,但莫名让人安心。
这段路不过二十多分钟,一眨眼就到了。
司机泊停在铁门门口,里头是典型的苏式园林建筑,白墙青瓦,嶙峋假山之上流淌着涓涓细流,木兰花茂盛的枝条耷拉在墙外。
由此也可以看出庭院主人是个颇有意趣的人。
出门迎接的是余枫的孙子余明意,他今年刚从国外毕业回国,还处于待业阶段,在老宅里陪爷爷。
他性格开朗,一句讲着笑话把客人带到会客的正厅。
余枫没有坐在正中央的沙发上,反而缩在西北一角的棋桌上,一手执黑一手执白,自娱自乐在下棋。
他染了全头黑发,面上是保养妥当的红润,蓄了一把小山羊胡还要染黑,精神矍铄得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
金丝眼镜后面的两只眼迷瞪着黑白子,一眼都不带搭理两人的。
余晏只觉四肢被冻僵,一股痛意盘旋在心口,且有要往喉头去的趋势。无他,余枫长得太像父亲了,他差点认为是老了十岁的父亲到了自己跟前。
压下这股气,他抬步走到棋桌前站定,低头琢磨了眼局势。
然后擅自从黑棋罐里取了枚棋子,钳在食指与中指之间。
“哒。”放下。
局势瞬转,白棋败势已定。
余枫很久没有遇到对手了,他推了下老花镜,低头思考良久,直到整个头都在塞到棋盘里面。“好好好,看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步棋走得绝妙,你是谁家的!”
他蓦然出声,很是感慨地抬起头想要看看这只手的主人,然后看到那张脸之后僵在了原地。
他喃喃道:“完了,肯定是我死期将近,大白天见鬼了。”
余晏:“。”
他设想过很多种跟侄孙相见的画面,或许是尴尬的,或许是伤心的,但就是万万没想到是上来冲自己喊见鬼的。
余枫一辈子从国外拼到国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临了没想到能见到跟自己叔祖父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脑袋被浆糊给蒙住,半点弯都转不过来。
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碰了下余晏胳膊,热的,活人。
“你你你你你就是联系我说知道余晏线索的那个人。”
席澍门口走进,很彬彬有礼地重复:“我我我我我就是联系你的那个人。”
“啊!”余枫两只眼睛瞪得溜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么大的情绪起伏了,此刻心脏撞得怀疑自己下一秒得进医院。
这跟老一辈留下来长辈里那张照片里的席澍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曾祖父的干儿子,祖父的干弟弟。
他手颤颤巍巍地指向席澍,抖着嗓子问孙子:“明意,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他是真实存在的吗?”
余明意莫名其妙:“爷爷,您是不是下棋眼睛下花了,他就是那位联系您的席二少爷,从西京来的。”
余枫狠狠闭上眼,他得消化一下这两张脸,不…这两个人是什么情况。亲的和干的叔祖父也没有后代啊,难不成是偷偷生的私生子,然后后代认祖归宗?
被称作鬼的余晏默了片刻:“老先生,我是余晏的后人。”
见他信誓旦旦的模样,余枫还是挣扎出一丝理智:“这不太可能,族谱里写得清清白白,我叔祖父没有后代,你别玷污他清誉。”
“……”余晏打好的草稿被这一句堵回去,“他……会不会有种可能性是无意之间的。”
余枫问:“什么说法。”
余晏狠下心玷污自己,张口就说——
“我是从爷爷留下的物件中翻出来日记才得知的,他母亲是戏楼里的花旦和余晏一夜情,自知配不上余家的门楣,所以怀孕之后偷偷生下孩子,本想养大些让他认祖归宗,没成想余晏死讯传来,这下没了证据,只好独自抚养。”
席澍以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向余晏,就像是谴责什么负心渣男。
忍受一秒后还没有消停,余晏手滑到他腰间,用力攥紧一拧,很凶地示意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