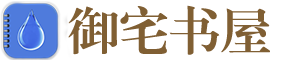第61章
作品:《捡到疯批老婆时》 是夜,沈瑾文散着发安静地躺在床上。
纵然浑身疲惫,她依然十分清醒。
辗转反侧许久,她平躺着,眸子中一片混沌的黑暗。
在说出那段话的同时,她便开始懊悔。
实在是关心则乱,怎么一张口就说了如此伤人的话。
这孩子也是想要保护自己。
她非但没有感恩,反倒不分轻重的责怪于她,这真是实属不该。
后台四敞,冷风直灌,在后半夜尤为明显。
她内心不安地坐起身,随意的披了件外衫,匆匆出门。
楼道昏暗,她举着烛光向下望去。
寂静的空间暗得人呼吸不畅,她突然涌上一阵不详的预感。
拢了拢衣摆,她焦急的快步下楼。
后台门前除了一片死寂,哪还有半点人影。
沈亦棠果然生了自己的气。
--------------------
第39章 破庙
手边是一个麻袋,沈亦棠慢悠悠地摇晃着腿,耐心地坐在一个巷口上的屋顶边。
拐角处的杨禄明一改往日高调的排场,左顾右盼一番,左脚后退拐进了巷子中。
这是一个死巷子,四周都是高大的房屋阁楼,衬得这一块即使是艳阳高照的白日也十分幽暗。
阴冷的环境让杨禄明叫骂了一句,两只手左右搓着取暖,嘴里还叫唤着,“小沈姑娘,小沈姑娘。”
“这特意叫人传话来约我见面,可是有什么好事想和哥哥分享呀。”
对方宛若从厨房刚出来的嗓音让坐在上面的人有些厌恶地皱起眉。
这人可真是阴沟里啄食臭鸡蛋而生的蛆虫。
她仅仅只是让叫卖的货郎替自己传话:有一位姑娘邀他去东街的巷口见面。
仅此而已的话语都能被这人臆想成沈瑾文。
指节微动,发出响声,她扯出一抹夸张的笑。
这种肮脏不堪的人到底哪里值得沈瑾文抛弃自己,让她没了安身之所。
思忖至此,她抓起旁边的麻袋,一个轻盈地跳了下去。
身后是一阵轻柔的脚步声,杨禄明嘿嘿的笑着,就在快要转头时被后面那人用袋子套住了脑袋。
这件事发生的太快,让杨禄明措不及防。
他呜呜的叫着,眼前一片漆黑。
他哐当一下跌坐在地上,双腿发软的颤抖着。
突然,腹部传来一阵剧痛。
紧接着那种痛不甚均匀的分布到身上的每一处地方,他被打的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凭着本能的不停嚎叫着。
对方的哀嚎实属刺耳,刚准备往那人脑袋去的拳头蓦地收了回来。
她无趣地站直身子,语调懒散地建议:“能不能不出声呢,你叫的声响可真难听。”
攻击自己的人拳拳到肉,力道大的让他骨子里都疼。
原以为是个与自己结仇的彪形大汉。
结果对方出声居然是个女子,还让他格外熟悉。
“你……你不是昨晚那个……”
“别再去找沈瑾文了。”她好心情地蹲下身,指尖挑开遮住对方的麻袋,沈亦棠直视着对方被自己打肿的眼睛,笑得人畜无害。
“不然不出一日,大街小巷都会知道杨国府的杨公子被一个弱女子给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和头丧家犬般躺在地上苟延残喘。”
“你觉着你身边的那群好友该如何看呢?”
面前这人说话的语气越是和煦,他那隐隐作疼的腹部就不自觉得抽搐,“知……知道了,知道了。”
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她满意地点点头,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既然太和楼不能再回,她也暂时没有再去寻得其他住处的想法。沈亦棠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晃悠着。
街市边琳琅满目的商品惹得人目不暇接,路上挤满了匆匆而过的人。
沈亦棠对这些并无兴趣,只是草草扫过几眼便离去。
踏过这段喧嚣的地段,越往前走周围的建筑房屋就越简朴。
冬日的白昼短暂,她也只是走着,天边就擦过了暗色。
怀里揣着两个白白胖胖的大馒头,她这条路的尽头卧居着一座破庙。
指尖即将推开那扇门时,她的耳朵动了动,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许动静。
大风冲撞得屋内呜呜作响,屋内的两只狸猫交颈缠缩在一起。
其中一只毛发湿漉,止不住地发抖。
蓦地,门外传来一阵亮光,有人走了进来。
靠在上面的那只狸猫警觉地站起身,脊背拱起地哈着气。
但很显然,这点威胁对于那个不速之客并无太多的威胁。沈亦棠不急不缓地跨步进来。
背着光的身影满满靠近,距离它们三步远的位置,她的五官逐渐清晰。
背光的人微微弯下腰,热心地问道:“我见你们貌似遇了麻烦,需不需要我来出一份力呢?”
*
干燥的柴火给予这座破庙难以忽视的暖意,噼里啪啦的烧着好不快活。
快要被大雪给冻僵的狸猫夫妇蜷着身子,嘴里发出舒适的呼噜声,睡在了沈亦棠身边。
翻出了埋在稻草中的一块石板,她把从雪地里扒来的草药用石头细细地碾碎。
清新的草汁粘稠地搭在石板上,也沾染了沈亦棠的手指。
不甚在意的用身上的衣料擦拭干净,她扯开了之间缠绕在手腕上的止血的布条,从腰际拿出刀,眼睛不眨地剐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