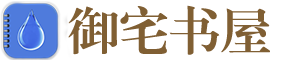上浮
作品:《情迷1942(二战德国)》 世界在那一瞬像被抽空了。
等克莱恩回过神时,河水已经没过头顶去。
水下是一片光怪陆离,玻璃、椅子、小提琴…还有四处漂浮的尸体和扑腾着的人——可就是见不到她。
暗流撕扯着军服,窒息感漫上喉咙,他只不顾一切往下潜。
直到视野尽头,撞进那抹晃眼的白。
她的黑发四散开来,周围萦绕着薄纱般的淡红,丝丝缕缕,细看才惊觉是血,正从她肩膀不断渗出来。
今早临走前,她迷迷瞪瞪地跑下来,还赤着脚,却偏要给他整理勋章,“别着凉了。”他当时皱着眉想说,话到嘴边却成了纵容。
他低头,鼻尖恰好埋进她肩窝,玫瑰香气漫上来,甜得让人心头发紧,忍不住就轻轻咬了一口。她瞬间红了脸,推着他肩膀。
“哎别闹,今天是要出门的。”
胸口突如其来的扯痛让克莱恩呛了口水。
这种对自己身体失去掌控的感觉,陌生得很。
去年隆冬,伏尔加格勒的雪深及膝,他们被五倍于己的T34坦克困在废墟里,他还能琢磨着半夜突围回大本营,能不能赶上伙房最后一锅圣诞热红酒。
攻进哈尔科夫时,他在森林里被苏联狙击手盯上,他还有闲心跟藏在树冠里的对手玩了半小时捉迷藏,最后用一发子弹结束了这场“游戏”。
“钢铁死神”的名号不是白来的,血火里滚过的人,早就该把心炼得比炮管还硬。
而现在,他划水的手却不知为何乱了阵脚。
直到触碰到她的那一刻。
指尖先撞上她冰凉的手臂,几乎是同时,她就抓住了他前襟,和过去每次做噩梦时抱紧他一样。
水里一切都很混沌,女孩微微睁开眼,隐约看到金色发丝在水中浮动,一股强大的力量拖着她,从深渊里带着向上升。
似乎连河水也变得温暖了些,她能感受到他胸膛传来的温度,是雪夜里她总抱怨“烫得睡不着”,却非要蜷进去才能闭眼的温度。
她小手往上摸,大约是摸到了他的脸,眉骨的棱角、鼻梁的弧度,还有下颌的线条,都和记忆分毫不差。
这不是幻觉。
“别睡。”
两个人纠缠着向上浮,克莱恩的声音隔着水波传来,她失血太多了,体温也在快速流失,随时可能陷入休克。
眼前不再是一片黑,起初是光斑,渐渐聚成一束光照下来,越来越亮,越来越暖。
哗啦——
破水而出时,空气争先恐后地涌入肺叶,克莱恩的脸庞近在咫尺,水珠从他眉骨滚落,滑过挺直鼻梁,悬在下颌摇摇欲坠。
他的眼睛,那双没表情时总透着几分冷的蓝眼睛,里面满满当当倒映着她的脸。
他终是来接她了,她想摸摸他的手,可眼皮越来越沉,连牵起嘴角的力气都抽干了。
黑暗笼罩下来。
刺眼的探照灯扫过水面,君舍眯起眼睛。
水花四溅中,克莱恩抱着人浮出水面,那个连走路都带着容克式傲慢的老同学,此刻狼狈得令人发笑——金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前,军装也浸透了,活像头落水的狼。
在这小兔面前,倒总能表演英雄救美,是不是下一步还得来给大家来一个人工呼吸?
君舍本想这样开个玩笑,可看清克莱恩怀里的女孩时,戏谑凝在了脸上。
那只小兔,现在正软绵绵蜷在他老伙计臂弯里,湿透的裙子紧贴着腰线,若是平时,他定会在心里调侃句“怎么比自家那小舞娘还要勾人”,但此时,那淡紫上晕开的暗红烙得他眼睛一黯。
她肩头有枪伤,嘴唇发着紫,苍白得像具瓷偶。
如果不是偶尔呛出两口河水,她现在这模样,和河面上漂浮的那些尸体实在没什么两样,更是和下午的娇花模样判若两人。
他莫名觉得领口勒得有些发紧。
下一秒,那朵被暴雨打蔫的紫罗兰就被遮了个大半,他的老伙计脱下军装外套,整个人俯下去,紧紧环抱着她,像要把自己体温都渡给这小兔。
而他的手也像被河水冻透了,竟在微微打战。
难以想象这个当年军校门门科目都是第一的传奇人物,能蒙眼十秒内组装枪械的老同学,现在活像只被拔了爪牙的猛兽,连急救包里的纱布都撕得七零八落。
她在他怀里越是抖的厉害,他的手也越不听使唤。
现在必须先解决失温,这个念头扎进克莱恩险些混沌了的脑子。
“毛毯!”
这一声惊醒了君舍,棕发男人这才后知后觉,女孩正因失血与落水承受着失温。
他抓过手边毛毯递过去。
那小兔的睫毛也随着身体在颤,与往日见他时如出一辙。只是那时,她低垂的睫毛下总含着一丝不服,让他永远猜不透那张兔皮下翻涌着什么狡猾心思。而现在…
君舍别过脸,他本该有点幸灾乐祸的,看着这个永远游刃有余的老友方寸大乱。
克莱恩用毛毯把女孩严严实实地裹住,再隔着毯子把她搂在怀里,直到怀中战栗渐渐平息,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他终于能分神处理伤口了。
这样的枪伤,对从维斯瓦河打到伏尔加河的克莱恩来说,本连眉头都不值得皱一下,他帮自己的兵处理过比这严重十倍的伤口,若是在自己身上,他大概抓把纱布一缠,就能转身跳上坦克继续冲锋。
可这是她的。
她那么怕冷,一到冬天就往他怀里钻,手脚凉得像冰块,非要焐到浑身发烫才肯罢休;她也是个十足的小娇气包,喝口热茶都要对着杯子吹上半天,生怕烫着舌尖。
她还格外怕疼,上次在书房,不过是被桌角磕了下小腿,就红着眼眶,非要他揉着伤处哄上半天,才把眼泪憋回去。
可现在,她的肩上却裂开一道口子,暗红的血水混着河水渗出来。
“该死…”
酒精棉刚碰到那血口子边缘,她就瑟缩一下,他的心跟着一颤,动作又乱了。
克莱恩不得不动用全身的意志力,才堪堪稳住手指。
周围渐渐嘈杂起来。救生艇上已陆续抬上其他伤员:汪伪驻德代办捂着血流如注的胳膊哀嚎,盖世太保保镖的大腿扎着块扭曲的弹片。
君舍踱到呻吟着的下属旁扫了一眼,不耐烦地啧了一声,“女士优先”,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刚拆封的医疗包。
声音还是漫不经心得很,眼神却越过克莱恩的肩膀,落在女孩毫无血色的小脸上,他打量起那伤口——啧,老伙计这包扎手法还真是烂得可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拆炸弹。
“要帮忙吗?”
克莱恩连头都没抬,他手上动作不停,更吝于给任何警告,只是侧了侧身,肩膀像一堵墙,将外来视线彻底隔绝在外。
月光落在他侧脸上,湖蓝色眼睛此刻淬了冰,他像头护着幼崽的雪豹,浑身都透着“生人勿近”的气息。
换作平时,君舍会识趣地后退,甩下一句“你们继续”轻飘飘带过,可现在他鬼使神差地又迈了半步,棕色瞳孔里闪过自己都未察觉的执拗。
两人间的空气像凝住了,直到一声呻吟从克莱恩怀里溢出来。
小剧场:
作者:这一届最佳电灯泡之多管闲事奖颁给…
汉斯:这次不是我了吧
奥古斯都:更不是我了吧
君舍:(默默磨刀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