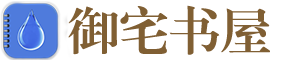新生
作品:《情迷1942(二战德国)》 夕阳的余晖包裹着那抹纤细身影。他静静看她,泪痕还挂在脸上,脊背却挺得笔直,像极了暴风雨后仍固执挺立的矢车菊。
忽然,琴声中断在了某个小节。
女孩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双手颓然落在琴键上,撞出一串杂音来,不知是不是心电感应,她倏然间回过头。
此刻,克莱恩的身影与暮色融为一体,看不真切。
她不自觉并拢膝盖,手指也无措绞在一起,像是回到了十多年前,被老师抓到指法错误的时候。
他听了多久。是从那个总是卡壳的转调开始,还是更早。那些错音、还有带着点发泄砸向琴键的强音,是不是全落进他耳朵里了?
他会不会觉得,这些天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她还是那个蜷在档案室角落里发抖的女孩?
男人在她面前站定,目光从她泛红的指尖,起伏的胸口,定在蒙着水汽的眼睛上。
“《悲怆》,选了个难的。”
俞琬垂下眼睫,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嗯”了一声。
下一秒,身侧微微一沉,他挨着她坐下,琴凳并不宽敞,他的腿紧贴着她的,体温透过衣料传过来。
他没看她,修长手指随意放在黑白键上。那双手,虎口处有常年扣动扳机磨出的茧,握惯枪械,签过无数处决令,这样放在这,倒有一种猛虎细嗅蔷薇的矛盾感。
“你弹得很好。”
俞琬怔住,睫毛轻轻颤了颤,他是在安慰我吗?
克莱恩是真心的,尽管说出口时,他自己都略微一怔。
严格从钢琴演奏的标准上来说,不是。
华沙阁楼里,他第一次听她弹贝多芬,那时的琴声是被精确切割的钻石,完美到像唱片公司一节一节找名家录制的示范带。
而现在那些音符,反倒让他看到了一把刚开了刃、带着生命力的刀。
“我们继续。”
女孩依言把指尖放回琴键。
不知是不是那句话的缘故,这次她放松了些,音符像完全解冻的春溪,开始自由流淌。
可就在一个关键转调处,她的食指又滞在半空,那个顽固的降B调像道坎,每次经过都让人屏住呼吸,一个不小心,指尖就会滑到其他地方去。
又要弹错了吗?
这念头升起的一瞬,一只手已越过她的肩头,按下她踩空的琴键,像踉跄时稳稳扶住她的手。
她惊讶侧头看他,而他的目光却落在她手指上。
接下来的演奏发生了变化。她依旧主导着旋律,但每当溪流遇到险滩暗礁,他总能适时加入,用低音或和声,为她铺垫。
他像一个领航员,在这片重新启航的水域中,指引着航道。
乐章终于浑厚的降A大调主和弦,女孩抬起发颤的指尖,心跳还没从方才的激烈里中平复过来。
而克莱恩的手指还停在琴键上,像在思考着什么——
随后《致爱丽丝》的前奏流淌而出。
俞琬呼吸一滞。
几百个日夜前,华沙那个小阁楼,三角钢琴落了一层薄灰,那时的她刚被他从军营带出来,她在和他冷战,把灰蒙蒙的情绪都诉诸于琴声。
彼时,她连当下该怎么过都尚且迷惘,更不敢去想他们还能一起走多久。
后来他在阁楼弹了巴赫,他们第一次说起彼此的童年,第一次四手联弹。
此刻,他依然先发出邀请,和那天一样。一种奇异的感觉冲得指尖有些发烫。
顿了几秒,她轻轻点头,指尖接续那段熟悉的前奏。
在一次双手不可避免的交错里,他的手背擦过她手腕,那触感让她指尖一滑,一个刺耳的音符冷不防跳了出来。
下一秒,男人的手指便掠过琴键,把那音符编织进一段即兴和声里,原本的失误,转眼成了独一无二的装饰音。
全然接纳,并化为整体的一部分。
俞琬眼眶莫名有些发热,旋律不知不觉彻底舒展开,那溪水越来越丰沛,终于漫过石滩,汇入更广阔的河床。
如果是这样呢?
她突然加入一个小变奏,把原本规整的节奏打散两拍,带着点儿试探,她仰头望向他。
克莱恩指尖立刻给出回应。
琴声越来越明亮。
她的手指开始跳跃,大胆踩下延音踏板。在男人第四小节的和弦里,她竟挑衅般加入一串颤音,要是在上海,布尔文斯基夫人听了定然要被气得晕过去。
克莱恩眼角弯了弯,骤然加重力道,低音如德军坦克碾过雪原压向她的颤音,而女孩不退反进,高音在进攻间隙里闪转腾挪。
他与她在这段即兴旋律里,尽情追逐着、嬉戏着,像在庭院里舞着一曲探戈。
没有言语,只有钢琴在代他们交谈。
暮色渐浓。
最后一个和弦的余韵弥散时,俞琬这才发现自己的脸颊烫得厉害。
克莱恩低下头,女孩微湿的鬓发贴在颊边,他伸手为她拂开,指节不经意擦过肌肤,那温度让两人都微微一颤。
下一秒,他把她紧紧拥入怀中。
花园里的灯亮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彻底糅合在了一起。
从华沙到巴黎,分离又重聚,穿过硝烟,经历生死,他们又并肩坐在琴凳前,时光在这一刻打了一个回旋。
还是那首曲子。还是他们。
可她的琴声早已不是当初那曲调,如今她敢失控,敢冒险,还胆子大到敢抢他的节拍,她破碎过,又自己拼凑起来,裂痕里长出了新的生命。
而他,竟该死的爱极了这样的她。
——————
俞琬真正走出来,是一个寻常的午后。
劫持事件后,巴黎戒严全面升级,为保险起见,他们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敢去取斯派达尔留下的情报。在丝绸行地下室里,温兆祥面色有点奇怪,他把一个木盒子交给她,说是将军留了纸条,专门给她的。
盒子很旧,锁扣已经锈蚀了。
她偷偷坐在三楼图书馆里,打开了它。
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信札,用细绳捆着,纸张泛黄,边缘微卷,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旁边是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记。
她拿起最上面一封信,落款是 “Nan,于南京”,在1936年秋。
信里字迹是英文书写,却带着中文的含蓄:
“亲爱的恩斯特,今天路过教堂,听见里面在唱《圣母颂》,忽然想起你离开那日,也是这样的天气。你说德国的森林在秋天如同燃烧的黄金,我总想象不出那景象,此间梧桐也开始落叶了,只是颜色要更沉些…”
恩斯特,那是将军的名字。
她一封封读下去。
信里没什么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南京的雨季,共同读过的书,对时局的担忧…字里行间,一个中国女子,克制而绵长地爱着世界另一端的一个人。
之后,她翻开了那本日记。
起初多是军事战略分析,间或掺杂着动植物素描和游记,直到某一页,出现了 Wang Hsiang-nan这个名字。
“1934年11月7日,于南京。今天遇见王湘南小姐。她笑起来时,眼睛像扬子江上的晨星。”
那些简洁的字迹开始有了温度。
“湘南说,我们之间隔着整个欧亚大陆,还有各自的家族与责任。她说得对。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心意。”
再往后。
“分别时,她送了我一块黑石头,叫Yan-tai(砚台),还教我认了四个汉字‘见字如晤’。”
他们最后怎么了?她是否活过了…南京那个冬天?唰啦唰啦,她急急往后翻。
1938年4月24日,汉堡。笔迹在这里变得极凌乱,墨水洇开,像是被什么液体浸湿过。
“她…”后面的字被狠狠划去,力道之大,几乎穿透纸背。“上帝已死。”
这一页的纸格外皱,像是被人揉搓又展开。女孩试图抚去那些凹凸不平,忽然间触到几处圆形痕迹。
是泪,六年前的泪。
日记最后一页,墨色不深,字迹却极稳:“六年了,南。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另一个世界或许没有欧亚大陆。”
女孩的泪水滚落下来,一颗两颗,洇在纸页上,与那些早已干涸的泪痕重迭起来。
最后,她拾起那张纸条,“给勇敢的小姑娘。”
“这是巴伐利亚的牛奶糖,和勇敢的小姑娘最配了。”这句话,忽然间穿越了时空,在耳边响起来。
一种奇异的平静缓缓覆盖了心中那片血迹,她合上日记,走到窗边,天空高远,远处铁塔静静伫立。
将军选择了离开,而他们,还活着。
楼下传来克莱恩回家的脚步声,战争没结束,未来依旧迷雾一般地不可测。
可就在这一刻,俞琬感到那些扼着她咽喉的梦魇,第一次,全然松开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