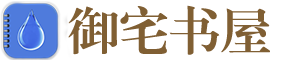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37)柳腰轻(中)
作品:《莫负好时光》 蕙宁陪着赵夫人妥帖地安置了表舅舅一家在东偏院,细细叮嘱了下人们饮食起居的安排,待一应妥当,赵夫人这才温声唤她:“你也乏了,快回去歇着罢。”
天气寒凉,日头斜照在廊檐间,到了初叁,蕙宁要随温钧野一道回娘家拜年。天气比往日更冷了些,地上的冰雪尚未融尽,晨风中透着清冽的薄凉。温钧野一身鲜艳正红色狐裘,意气风发,十分醒目,马车里缠着蕙宁想让她在自己颈边布料上头绣一朵并蒂莲花。
吴祖卿亲自迎出门,满面喜色,他年事已高,精神倒还矍铄,言谈间依旧风骨犹存,只是声音微微沙哑,行走也不再像往年般利落了,蕙宁心里总是有些酸。
陈轻霄抓着温钧野又要比试刀法,现在倒好像是成了好兄弟。不过因为是过年,被吴祖卿给拦住了:“大过年的舞刀弄枪吓不吓人,等着年过完了,你们俩找个校场,酣畅淋漓地比试一番。”
吴祖卿年岁已大,近些日子也考虑想辞官,陈轻霄在身边,吴祖卿的意思是想让孙子陪着自己回从前妻子的老家去看看,凭吊一番。说着,他叹了口气,目光深沉如井:“这些年皇上一心栽培太子。太子虽生得温文尔雅、端方有度,倒是有几分帝王的相貌。可性子太软了些,处事太过谦恭周全。明王却不同,那是锋芒毕露之人。如今宫中内外,皆知他虎视东宫。这风雨将至之势,终究是藏不住的。”
厅中一时静了下来,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应和着这话中暗流。
吴祖卿目光微转望向温钧野,神色凝重几分:“我听说你与那小明王……曾有些过节?”
温钧野挑眉一笑,只是轻松说着:“不过是马球场上互有胜负,争个高下罢了,不至于算仇。”
吴祖卿却摇头,话语低缓却沉稳,语重心长说:“少来往得好。你们都是出身名门,越是这时候,越要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人该远。”
温钧野听得认真,当即点头:“外公所言极是。我本也不喜明王府上的做派。”
说话间,天色渐暗,晚风透过窗缝吹进厅中,火光摇曳。蕙宁扶着外祖父回房,顺势提起上回奉婆母之命前去明王府邸修补关系之事。她叹口气,唏嘘说:“那府邸确实是奢靡非常,金玉铺地,雕梁画栋,竟比宫中还要气派几分。陛下一贯提倡节俭,这般张扬,未免……打了皇上的脸面。”
吴祖卿微微皱眉,低声道:“你婆母的亲妹子虽是昭妃,可年纪尚轻,又无子嗣,地位看似尊贵,实则底气不足。可明王的妻妹薛贵妃,却实打实是有个皇子。皇子尚幼,若有人为他筹谋,将来未尝没有可能……”
他声音低了些,仿佛怕被风听了去:“温国公生性淡泊,不喜与人结党,向来只想着独善其身。可你要记得,宫里头的风一日叁变,你们两府的关系未必能修得成。”
蕙宁轻蹙眉心,轻声道:“我那日在宫中也遇到了薛贵妃,确实是好大的气派。可我婆母从不插手朝政,他们凭什么就能无端来为难我们?”
吴祖卿叹息一声,言语中藏着几分无奈与警醒:“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眼下太子虽尚安稳,可朝中风向已然有了微妙变化。东宫若有变,国公府权大势大,就算不与东宫来往,也终归不能独善其身。”他说罢,顿了顿,似怕吓着她,又摆摆手轻声道:“也可能是我这把老骨头胡思乱想得多了。世事无常,未必真有大变,说不准终究风平浪静。太子顺利登基,一切都平稳无波。”
吴祖卿拍拍她手背,语气一转,带了几分慰藉:“说来说去,我最记挂的还是你和轻霄,我瞧你和温钧野的关系倒是越来越好了。”
蕙宁颊上浮起薄红,似叁更天雪地里燃起的一盏绛纱灯,低声道:“其实,是我从前对他有些偏见。”她眼眸微垂,深思熟虑一番,还是诚实地与外公说着:“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性子太硬,直来直去的,不会拐弯,也不懂人情世故,话说得重了,常叫人生气。但……这也正是他难得的地方。他的真诚,是藏不住的,对我也从不设防,从来没有一句虚言。”
她顿了顿,睫毛轻轻颤了一下:“所以……我也慢慢改观了,觉得他,其实很好。”
吴祖卿凝视着外孙女那含羞的神色,目中渐渐生出欣慰。他叹道:“他有想过今后该走哪条路?难不成真就一辈子做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
蕙宁笑了笑,自家相公还是需要自家娘子的袒护:“我想他有自己的抱负,也有一番天地,只是他不说而已,不急。我也会陪着他,一起谋划的。”
吴祖卿凝视她一瞬,终是点了点头,笑意里掺杂着些微的感慨与怜惜,缓缓抬手,轻轻摸了摸她的脸颊,声音低沉却温暖:“好,外公信你。你从小稳妥聪慧,有你的主张,自己的家,你自然也能打理好。”说着,他从案几上抽出一张纸来,边递边道:“这是我替你拟的几位教书先生的名单,个个有家学渊源、人品稳重。你拿回去与你公公婆婆商量着看,别在这等事上出差错了。”
蕙宁双手接过,语气恭谨中带着亲昵:“多谢外公体贴。”
吴祖卿摆摆手,像是说起了最寻常不过的事:“外公不帮你,还能帮谁去?”
黄昏的天光浅浅地铺在窗棂之上,屋内的灯火早已点起,光影间,温情宛然。二人本打算留在吴府用了晚膳再回,怎料这时便有吴府小厮匆匆进来回报,说国公府那边派人来了,好像是有点要紧的事儿,要他们夫妻二人即刻赶回去。
来禀报的是赵夫人身边的贴身丫鬟,吴祖卿顿觉情形不对,当即沉声道:“事急就先回吧,反正离得不远,你们随时都能来。”
温钧野与蕙宁不敢怠慢,草草告辞,立刻登车回府。夜风冷冽,马车在雪泥中辚辚而行,仿佛也察觉了气氛紧张,一路无声。
到了国公府,厅堂只开了一扇门。火盆燃得旺盛,暖意未散,却压不住那室内沉沉的气息。赵夫人正襟而坐,神情铁青,一双眼睛似要将人穿透,连那一向含笑的嘴角,此刻都绷得紧紧的。
堂下地砖冰凉,一名少女跪伏在地,衣衫不整,发髻散乱,肩头半露,像一朵被风雪碾碎的落梅,泣不成声。正是前几日方被安置在偏院的表小姐。
她的父母——两位表舅与表舅母,此时也在场,二人脸色极其难看,像是羞愧,又像是怒不可遏,却也藏着不易察觉的、孤注一掷的喜色。
蕙宁与温钧野对视一眼,心头已有几分猜测。两人未敢贸然发言,只悄悄与赵夫人身边的嬷嬷交换了几句,这才听清原委——
原是今夜温钧珩因年节繁杂之事,再加上妻子生病,独自歇在书房。未曾想这位表小姐竟趁夜以“送果子”为名,径直进了书房,不知如何纠缠拉扯起来,等下人闻声赶去时,只见她衣襟凌乱,带子松垮,白生生一截肩膀露在外头,甚是尴尬。
温钧珩当场气得面色铁青,差点要动手,还是小厮死死拉住他,才未闹出更大的祸端。
听到这里,蕙宁的脸色也沉了下来。温钧珩是个寡言的人,性子沉稳,素来最讲分寸,而且一心一意对自己的妻子,如今竟会气得动手,可见此事绝非无风起浪。
果然,表舅舅得知实情后,当即破口大骂,扬手便给了女儿一记响亮的耳光,骂她是不孝之女、丢人现眼,打得表姑娘像一朵逶迤在地的蔫花,连哭的力气都没了:“要不是看在祖上情分,今日就把你活埋在雪地里,就算我不曾养过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蕙宁自小长于书香门第,父母和外祖父那里都没有类似的情况,表哥也是洁身自好,到现在也没定下心来,故而从未亲历这等家门风波。厅中一地的沉默与哭泣,仿佛压得空气都凝滞了。她与温钧野虽是新婚小夫妻,这等情势下也觉进退维谷。
温钧野斜倚在一旁,眉眼冷冷,神色早已沉似寒潭。方才那嬷嬷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此刻轻哼了一声,目光扫向屋内那几人,冷峻中带着些许厌烦。
嬷嬷贴近蕙宁,声音压得极低,却急切中透着几分担忧:“叁少奶奶,如今您掌家,虽是大爷房中的事,您也不能坐视不理。况且夫人方才气得直抖,我是怕这事闹大了,真有个好歹……这表姑娘,年纪不大,心思却不小,做出这等事来,实在……实在不像话……”
温钧野嗤笑出声,眸中冷意一闪:“不就是不守规矩?拖出去打上一顿便罢,哪来那么多事?”
嬷嬷面色一变,连忙低声劝着:“叁少爷,这打是万万使不得的。毕竟她是夫人娘家的姑娘,若真伤了颜面,怕是不好收场。面子上,总还得留叁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