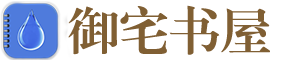第二十章避子
作品:《罰紅妝》 辰时初,宋楚楚终于睁眼,在榻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娘子,您起来了。早膳已备好了。」杏儿笑吟吟的迎上前。
宋楚楚揉着手臂坐起,脸颊还带着一抹淡红。昨夜湘阳王……又心血来潮,把她绑了个结结实实,折腾得她浑身酸软。
幸好湘阳王尚算体贴,从不真要求她早起侍候。
今日的早膳有桂花糯米小饭团,蜜渍金桔,燕窝冰糖羹。
宋楚楚吃得心满意足,唇角边都沾了点金桔糖浆。
待杏儿收了碗筷,她才微微蹙眉,总觉得似是少了些什么。
思考片刻,才想起——
「杏儿,避子汤呢?」
杏儿闻言,拍了拍额头,兴奋道:「都忘了稟告娘子了。王爷今早吩咐,从今日起撤了娘子的避子汤!」
这话一出,宋楚楚手指顿了顿,眼里微微一亮。她下意识地抬手抚向小腹,指尖轻柔,彷彿已能感受到未来某种温热的生命在那里跳动。
可那抹喜悦只维持了片刻,便被一股无声的闷意悄然湮没。
近日府中风声渐起,说湘阳王有意立正妃——虽未对外明言,却已传得沸沸扬扬。还听说前些日子,有位刘姓贵女被他带入府中,在正院现身。虽无人明讲她的身份,但眾人心中已有猜测。
宋楚楚咬了咬唇。立妃在即,自己这点宠爱怕是撑不了多久。
避子汤被撤,她应该高兴的。可心底却泛起莫名的酸意与怯意。
李嬤嬤曾言,王妾所出的孩子,若非嫡母身亡,大多都得交给正妃抚养。妾室无权教子,更无法亲自抚育。她自己便是庶女,自幼被侯夫人冷眼看待,什么委屈没吃过?
若真有了孩子……自己又凭什么保他周全?
宋楚楚垂下眼,手慢慢收回,掌心掐得微微泛白。原本甜滋滋的早膳,此刻竟像压在心头的一块石。
二日后申时,天气闷热,宋楚楚坐不住,便遣走了杏儿与阿兰,自己漫步至偏廊小院。她早打听过,这时辰灶房那头的小丫头阿桂常会提着药篮,把厨下所需的草药送去后院药柜,一边送一边顺手整理,是府中少数经常接触药材、嘴巴又不那么紧的下人。
见四下无人,宋楚楚轻声唤住了她。
「阿桂,你先别忙……我问你一件事,只问问,不是叫你做什么。」
阿桂一脸懵懂:「娘子儘管吩咐。」
宋楚楚迟疑片刻,终是压低声音问:「那避子汤……我听说都是由药房配好,送来的。若……若有人想继续服用,要怎么才拿得到?」
她话一出口,脸颊便涨红了。说得委婉,其实是直问「怎么偷拿」。
阿桂吓了一跳,支支吾吾:「这……奴婢不知……不过上次好像听说,春桃姐曾帮二嬤嬤领过——」
「嘘——你小声点!」
宋楚楚心乱如麻,自从那日向阿桂探询避子汤之事后,便夜夜难眠。
她其实也知自己鲁莽——那般话,说出口便已越矩。真正叫她付诸行动,她更迟迟不敢……只怕踏出那一步,便是万劫不復。
此后她再未提起此事,连杏儿与阿兰都察觉她神情恍惚、心事重重,却又不敢问。
这日黄昏,天气乍暖还寒,宋楚楚正坐于怡然轩的窗边,挽着衣袖,细细为一张綾纸上色。这是她近日间来练笔的小花鸟画,手中细笔点到鸟喙时,便闻廊外传来几声低低的「给王爷请安」,紧接着便是细碎的脚步声。
宋楚楚忙放下画笔起身,还来不及理好衣襟,湘阳王已步入殿内。他步履从容,面色淡淡,袁总管紧随其后。
她行了一礼:「见过王爷。」
「起来吧。」他语气不冷不热,眼神落在她桌上的画纸上,淡淡瞥了一眼,随即转开目光。
宋楚楚瞧着他,又偏头望了眼站在一侧的袁总管,心中隐隐不安。
湘阳王是怡然轩的常客,袁总管却不是。
这时,小廝捧着托盘进来,交予袁总管。袁总管沉默地将托盘搁于桌上。盘中是一碗汤药。
湘阳王落座,将身一倚,朝那碗药抬了抬下頷,语气平静:「喝了。」
宋楚楚盯着那碗热气腾腾的汤药,迟疑片刻,低声问道:「这是……什么?」
湘阳王闻言,声音清冷,字字如刀:「你不是在找避子汤吗?」
她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亲王续道,语气不疾不徐,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惊的寒意:「这里有一碗更好的。喝了,一劳永逸——绝子绝孕,往后再也不需避子汤。」
他语气平静得冷酷,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宋楚楚一听那句「绝子绝孕」,脸色倏然惨白,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颤:「不……妾只是一时糊涂,妾不想——」
湘阳王未语,只冷冷看着她,彷彿在等她自己崩溃。
袁总管一挥手,两名小廝即刻上前,欲按住她。
宋楚楚倏地挥袖,强自镇定地喝道:「走开!」
她随永寧侯学过几年武,情急之下反应极快,手肘一拧,竟将一名小廝撞得跌退几步,另一人也被她反推撞倒在案几边角。
袁总管一惊:「娘子,莫要自误——」
宋楚楚退至榻前,面色苍白,眼底满是恐惧:「王爷……妾知错了……求您饶了妾这一回……」
湘阳王终于动了。
他自座上起身,一步步走向她,神色阴沉得几近可怖。她心底一阵颤慄,却也不敢逃,只能紧紧抱住自己。
他站定在她面前,垂眸俯视,声音冰凉刺骨:
「无妨——本王亲自来。」
话音未落,他已一手扣住她后颈,将她拽至桌前,力道之重使她顿时动弹不得。瓷碗贴上唇边,热汤灌入,她喉头被迫张开,整个人惊惧万分,双手紧抓他的衣襟,指节发白,泪珠沿着脸颊止不住地滚落。
她剧烈咳嗽,却无力反抗。
一碗汤药灌尽,他才松开手。宋楚楚整个人瘫坐在地,颤抖如叶,唇色褪尽,眼中水光氤氳,竟连哭声也哑了。
「王爷……」她一边咳嗽,一边含糊带哭地问:「这、这碗……真的是……绝子药吗?」
湘阳王立在她面前,居高临下,长久未语。
她声音几乎断裂:「妾知错了……不该动这种心思……可若这药当真会让妾终身不能为人母……那妾……妾该怎么办……」
她忽地爬跪上前,拉住他的衣袍,泪水滚落如珠:「妾以后再不敢了……王爷,求您,求您告诉妾……可有法子能补救?可有一线馀地?」
她一句一问,几乎是用尽了力气。
湘阳王终于俯身,伸手捏起她的下頜,与她四目相对,语气冷冽:
「倘若你真敢暗中服药,那后果你承不承得起?」
他顿了顿,见她眼中满是惊惧与懊悔,这才缓缓道:「你方才喝的,是沉大夫今晨所配之方——养血调经,温补气脉,极适备孕。」
宋楚楚猛然一怔,整个人僵在原地,惊魂未定。
他甩袖而起,语气冷淡如常:「禁足三日,好好反省。三日后,来书房请罪。」
说罢,他转身离去,袁总管亦随之退下,内室一片静默。
三日后——
书房内,烛火静静摇曳,昏黄的光落在湘阳王沉稳的侧顏上。
他坐于案后,手中未执笔,只是长久地凝视着几张展开的纸张。
他看不透宋楚楚心中所思。每每以为她已然收敛,转眼却又行出叫人措手不及之举。
打探避子药——她这是哪来的胆子?
案上的画纸从怡然轩带回——他吩咐袁总管去寻,杏儿便交出了宋楚楚近日习画之作。纸上花鸟轻盈,笔触未算老练,却已见用心。
湘阳王一张张翻阅,最初只是随意一扫,直到翻到几张人物轮廓时,手指微微一顿。
头一张,是他。画中他头戴发冠,神情凝肃,身形挺拔,只勾了眉目与轮廓,并未细描。
第二张,是他卸去朝服后的模样,发未尽束,一缕乌丝垂落肩前,那是只有在内室她才见过的样子。
他心中微动。
直到他翻到第三张,画中人换了。
是永寧侯。
一张披甲立姿,鎧甲斑驳、笔势锐利;一张便服小像,眼角含笑,鬓边几丝银发细描入微,连眼尾皱纹也未遗漏。
湘阳王指节轻叩桌案,灯火下,他眸中一丝阴影悄然扩散。
画他处处节制,如临深渊;画她父却情感流淌,笔笔落情。
这点差距,看似无意,却让他胸口微闷。他忽地意识到——宋楚楚心中那最柔软的依恋,从来都不是给他。
他神情未变,继续往下翻。
便见一朵笔触细腻、姿态舒展的野花,细蕊微卷,花瓣开得极有韵致,色彩斑斕却不俗艳。
他认得这花——夜寒草,边关苦寒之地独有之物。
他四年前曾因西北补给之事驻守边关三月,见过那花在雪地中孤然盛放,极柔,也极倔。
他突然想起宋楚楚的话,伴随着那恣意的笑容——「王爷,妾随爹爹在边关住过几年,会骑马的。」
当时乍听之下,他并未在意。如今细想,愈发不是滋味。
他伸手将画按回案上,指尖微紧。那一瞬的动作几近温柔,却裹着难以言喻的压抑与冷意。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袁总管低声稟道:「王爷,宋娘子已到。」
湘阳王语气平静,未抬眼:「让她进来。」
门被轻轻推开,宋楚楚穿着一袭淡桃色襦裙,神色忐忑,行至书案前福身叩首,声音轻细:「见过王爷,妾特来向王爷请罪。」
湘阳王未即抬头,声音平淡如常:「起来吧。」
宋楚楚应了一声「是」,缓缓起身,站定原处,却不敢多看他一眼。
她垂着眼,馀光偷偷一扫案上,见那几张纸张半展未收,心头一紧——她认得,那是自己的练习画。画花画鸟的几张在上,还有几张人物轮廓……
她心头一跳,下意识地握紧衣角——那几张王爷与爹爹的描稿……杏儿怎会交上去?
书房静得落针可闻。
湘阳王终于抬眼,视线扫过她面容,落在她眼下那一抹红肿与倦意上,语气平静无波:「这些画,你都认得吧?」
宋楚楚心口一窒,低声道:「回王爷,是妾近日练笔所作……若有不敬,妾愿受罚。」
他挑眉一笑,视线落在纸上,声音含着几分讽意:「不敬倒也谈不上。只是,本王头一回见妾画主君,只勾轮廓;画父亲,却描得细緻入微。」
她猛然抬头,脸颊瞬间白了一层,语气带着慌乱:「妾、妾不是这意思……只是……」
「只是什么?」他接声而出,声音不重,却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她更慌了,连忙福身低头:「妾知罪……妾不该画得轻重失当,妾……」
他驀地打断了她:「本王记得,你曾居边关?」
话锋骤转,令她一怔。宋楚楚小心回答:「是,妾九岁丧母,爹爹忧侯夫人容不下妾,遂带妾去边关。至十四岁那年,他说妾已长大,不宜久居军营,便送妾回京。」
湘阳王沉吟片刻,终是冷声啟唇:「永寧侯自以为体贴,却未曾细思,将一女儿家置于满营铁血之地,日久年深,终教她成了什么模样。」
宋楚楚低头不语。她能感受到他语中的不悦,却又说不上来他究竟在气什么。
「于边关五年,都做些什么?」
「也就……骑马、学鞭、听将士们说边关故事、看星星……」
湘阳王闻言,冷冷一笑:「听来倒是比王府自在得多。」
语毕,他起身绕案而行,步步逼近,在她身侧停下,语气仍淡:「今日请罪,请的是哪一桩?」
她一怔,心头怦然乱跳。
他俯身逼近,声音低如碎冰:「是背着本王问避子药,还是——背着本王,心怀他念?」
宋楚楚猛地抬头,眸中带着错愕:「妾心里……只有王爷……」
「只有本王?」他语声一沉,冰意潜伏其中:「得宠却避孕,承欢却藏心。你说『心悦』,依本王看来,不过是图得安稳。若非无路可走,你岂会留在这府里,不随你父亲回边关过你的自在日子?」
宋楚楚几乎是惊慌失措地跪下,泪水瞬间涌满眼眶:
「不是的!妾心里只有王爷,绝无二心……」
她抬手覆上小腹,声音发颤:「妾也想为王爷孕子,只是……李嬤嬤曾说,妾室所出的孩儿,将来都得交由正妃抚养。」
她小嘴一撅,泪珠啪嗒掉落:「王爷快要立妃了,不是吗?如今连正妃是谁都还未明……」
语气愈发委屈:「妾也是庶出,从小受侯府大房的白眼、冷落。妾怕……将来孩儿若也如此,日日受人轻贱……」
说着居然低低地抽泣起来。
湘阳王蹙眉,神情愈发复杂。那一丝怒意似被她的眼泪微微软化,却转瞬又被心底更深的一层愤意吞没。
他抬起她满是泪痕的下巴,声音寒凉如铁:「宋楚楚,你是在说——本王的骨血,进了宗簿、冠了王姓,还会比你在侯府过得不如?」
她浑身一颤,只觉愈辩愈错,唇动欲言,却终究无声。
「你怕的,既非王府之制,亦非正妃之名……你是认定,本王护不住你与孩子。」
语毕,他怒极转身,袖袍翻飞,冷声丢下一句:「跪够了,便滚回怡然轩。」
说罢大步离去,未再回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