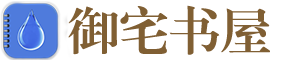陪伴(本文是初稿,因为看着不错就没花心思
作品:《龙与凰(百合.gl.1v1.伪快穿,轻H)》 晚上十点。
FADE酒吧的空气,比调酒壶里的冰块还要冷。
爵士乐的鼓刷声像幽魂,小心翼翼地摩擦着某种易碎的情绪。
这是白曦出现在这里的第七天。
凤九站在吧台后,用一块雪白的软布,一遍遍擦拭着那只已经光洁如新的古典杯。
她的动作是这里唯一的动态,黑色真丝吊带裙下滑腻的肩线,是唯一的风景。
那抹刺目的正红色口红,是这片冷色调里唯一的、固执的火焰。
她没看白曦,但白曦的目光,七天来每晚都准时落下,像这里的灯光一样,安静,且没有温度。
她们隔着叁米宽的黑檀木吧台,像一场心照不宣的对峙。
这场实验,进行得悄无声息。
终于,她停下了擦拭的动作,将杯子倒扣在吧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类似句点的声响。
她抬起眼,目光越过你的肩膀,看向吧台后那一整面墙的镜子。
在镜中,她第一次,正视了白曦的倒影。
白曦穿着洁白的衣裙,雪色长发随意的飘散,她浅蓝色的眼瞳里,充满了孩童的好奇与澄澈。
她大着胆子坐在了凤九面前的高脚凳上:“姐姐,能给我调一杯酒吗?”
凤九的视线从镜子里缓缓移开,最终落在了吧台前的白曦身上。
那双金红色的眼睛里没有情绪,既没有因为那声“姐姐”而泛起波澜,也没有因为这七天来的第一次对话而感到意外。
她的目光直接而锐利,像是要穿透白曦那纯洁无瑕的面孔,探究其后的动机。
沉默持续了大概五秒,长到足以让空气中的爵士乐变得有些刺耳。
终于,她纤长的手指在吧台上轻轻一点,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声响。
然后,她那涂着正红色口红的嘴唇微微开启,吐出的字句没有一丝温度,像冬天清晨的薄雾。
“你成年了吗?”
这不是一个疑问句,更像是一个程序化的确认。
她的声音很低。
白曦乖巧的点了点头:“嗯嗯,成年啦!”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凤九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她的目光在白曦脸上停留了两秒,那双浅蓝色的眼瞳,干净得像一块无瑕的水晶。
凤九的视线微微下移,扫过那身洁白的衣裙,最终,她像是失去了所有兴趣一般,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留给白曦的,只有一个冷漠修长的背影。
凤九从酒架的高处取下一支典雅的玻璃瓶,瓶中装着透明的液体。
接着,是冰桶里冰块碰撞的清脆声响。
全程,凤九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姐姐,为什么调酒要在那个小瓶子里呢?”少女好奇的声音响起。
摇晃调酒壶的动作猛然停住。
这个突兀的问题,让凤九背对着白曦的身影僵硬了一瞬。
她没有立刻回答。
她的瞳孔里,映出酒架上排列整齐的各式酒瓶,光怪陆离,井然有序。
‘那个小瓶子?’,她甚至觉得这个形容有点可笑。
她缓缓将手中的摇酒壶放在吧台上,嘴角嘲弄的弧度更深了一些。
“这是摇酒壶。”
她开口,声音平直,像是在纠正孩童一个可笑的错误。
“用来混合、冷却、稀释酒液。”
她用嘴简洁冰冷的陈述句,回答了这个问题。
随后便不再看白曦,重新拿起摇酒壶,准备将酒液滤入杯中。
那姿态仿佛在说:你的提问时间,结束了。
白曦看着那杯酒,歪了歪头:“姐姐,这杯酒多少钱呀?”
凤九正专注地将摇酒壶中的酒液滤入杯中。
‘又一个问题。’
她眼角的余光能瞥见吧台前那个歪着头,满脸天真的身影。
这已经是今晚的第叁个问题了。
对于一个习惯了沉默的人来说,这堪称是一种骚扰。
她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在最后一滴酒液完美注入杯中后。
她放下摇酒壶,拿起吧台上一片预先切好的柠檬皮,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捏,一股清新的油脂被挤压出来,喷洒在酒液表面。
做完这一切,她才抬起眼睑,将那杯鸡尾酒用指尖推到了白曦的面前。
杯子在光滑的台面上滑行了一小段距离,停在了白曦的手边。
“酒单在你左手边。”
她的声音依旧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没有继续看白曦,自顾自地拿起之前那块雪白的软布,开始擦拭刚刚的摇酒壶。
白曦默默闭上嘴,瞪着大眼睛看那杯鸡尾酒,眼神里面充满了好奇。
她拿起酒杯,好奇的喝了一小口,小脸瞬间通红,吐吐舌头,盯着酒杯好像在看什么奇怪的东西。
凤九抱着手臂靠在酒柜上,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看着白曦毫无防备的喝下一小口,她的眼神没有丝毫变化。
但当那张白净的小脸瞬间张红,还带着孩子气地吐了吐舌头,凤九的眼神深了那么一瞬。
那不是一杯烈酒,那只是一杯醉简单的金汤力,清爽,能很好的掩盖酒精的辛辣。
对她而言,这杯酒和白水没什么区别。
但对白曦这种的一张白纸来说,即使是稀疏过的墨水,也足以留下清晰的印记。
凤九看着白曦那副杯酒精突袭后,有些不知所措却又强装镇定,更加细致观察酒杯的模样,那总是维持着冷淡弧度的唇角,极其细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
“那是金汤力。”
她像是在解释,有像在自言自语,目光落在白曦通红的脸颊上,
“看来你不适合喝酒。”
白曦听了,不信邪的又喝了一口:“呜哇,好辣。”
那声带着鼻音的“呜哇”,像石子投入了凤九那死水般的心湖。
没有激起波澜,但确实让水面泛起了看得见的涟漪。
她的眼神变了,那双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饶有兴趣的观察。
像一个厌倦所有千篇一律剧本的导演,突然在片场上看到了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素人演员,充满了原始生命力。
她看着白曦那张因为酒精和辛辣而愈发通红的小脸,那双被水汽变得更加明亮的浅蓝色眼瞳,以及那副明明受不了却偏要再试一次的固执又天真的神态。
一种荒谬感油然而生。
“那你为什么还要喝。”
白曦红了眼:“花钱了,不能浪费。”
‘花钱了,不能浪费。’
这个答案,简单,直白,甚至带着一点小孩子的认真和计较。
凤九的手几不可查的蜷缩了一下。
她见过太多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喝酒。
为了庆祝,为了遗忘,为了麻醉,为了炫耀,为了社交……
但她从未听过这样一个理由。
如此的纯粹,如此的荒唐。
她看着眼前这张因为酒精而红扑扑的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写满了对‘浪费’这件事的耿耿于怀。
这一刻,凤九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悄然融化。
那是一种被遗忘了很久的情绪。
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被某种笨拙而真实的东西触动的感觉。
她伸出修长的手指,越过吧台,将那杯金汤力拿了回来。
她迎上白曦那写满不解的小眼神:“这杯,我请。”
白曦瞪大了眼睛:“可是,它已经被做出来了。”
那双瞪大的,写满固执的浅蓝色眼睛,直直的映出凤九冷艳的面容。
‘可它已经被做出来了。’
又是一个简单到近乎执拗的逻辑。
凤九握着冰凉的杯壁,她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了一下。
她见过无数精于算计、言辞华丽的人,他们会用一百种方式来试探、来索取。
但她从未见过这样的人,用一种笨拙到可笑的原则,来对抗她的决定。
凤九看着白曦那‘你怎么能这样’的委屈表情。
她沉默了。
那双总是锐利的眼睛,此刻竟微微垂下了眼睑,避开了那道直白的视线。
在白曦惊讶的眼神注视下,她抬起手,将那杯被白曦喝过的金汤力凑到了自己的唇边,她微微侧头,就着白曦刚才喝过的杯沿位置,仰起优美的脖颈,将杯中剩余的酒液,一饮而尽。
冰冷的液体划过喉咙,带着杜松子的清香和白曦唇上残留的一丝甜。
她放下酒杯,轻轻舔了一下自己湿润的唇。
抬起眼,目光重新锁定在白曦那张因为震惊而微微张开嘴的脸上。
“现在,它被喝完了。”
“没有,浪费。”
白曦缩了缩脑袋:“可是,它是我点的,理应谁点谁喝呀。”
那副缩着脑袋,小声辩解的模样,像一只被抢了坚果后,敢怒不敢言的小松鼠。
凤九的的心脏,像被捏了一下,不疼,但很无措。
白曦的逻辑,坚固得像一块顽石,不为她的所作所为动所摇。
那套在凤九看来幼稚可笑的原则,此刻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她自己的蛮横和失控。
她第一次,在一个人的面前,感到了词穷。
凤九看着那双因为委屈而愈发显得水汽蒙蒙的浅蓝色眼睛,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想抬手揉一揉那颗银白色的脑袋。
这个念头如此荒谬,让她感到一丝震惊和一丝恐慌。
她伸出手中,用指甲轻轻敲击着空了的玻璃杯,发出‘叮、叮’的轻响,像是在为自己的思绪打着节拍。
最后,她放弃了争辩。
她换了一种方式,一种她更熟悉的方式——交易。
她微微向前倾身子,黑色的真丝裙摆随着她的动作,在吧台边缘滑出一道危险的弧线。
她压低了声音:“那么,作为‘抢’了你酒的补偿。”
“你明天还来,我给你调一杯,真正适合你的,不辣的酒。”
她顿了顿,嘴角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
“并且,免费。”
她将这场逻辑的争辩,巧妙地转化成了一个由她主导的约定。
白曦像是被突如其来的靠近吓到了,声音怯生生的:“姐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一句话,像一根淬了冰的银针,刺破了凤九精心维持的所有伪装。
‘好?’
这个字眼,对凤九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如此的讽刺。
她所有的行为,从最开始的冷漠,到后来的讥讽,再到此刻带着强制意味的‘补偿’,都源于一种她自己都不理解的被打乱的节奏。
她只是想重新夺回主导权,想用一种她熟悉的方式来终结这场让她感到失控的对话。
可是在对方的眼里,这竟然被解读为了‘好’。
凤九前倾的身体猛地僵住,瞳孔在一瞬间剧烈收缩。
一股凉意从脚底窜起,瞬间包裹了她的心脏。
触觉错位,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
白曦这句天真的问话,像一个错误的信号,瞬间激活了她深埋心底的创伤。
她仿佛又看到了不渝,那个在阳光下身体冰冷的友人,也曾用这样不含杂质的眼神看着她,问她,为什么我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而最终,她所有的好,都变成了见证灾难的酷刑。
凤九缓缓直起身,重新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去,只剩下那抹刺目的红唇,像雪地里的血迹。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拿起台上的软布,用力擦拭玻璃杯。
“我不好。”
她抬起眼,目光里所有的情绪已经退去,只剩下最初的冰冷。
“而且,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你欠我一杯酒,明天记得来还。”
说完,她不再看白曦一眼,转身走进了吧台后方那片最深的阴影里,只留下一个决绝而孤寂的背影。
白曦望着她的背影,委屈的嗫嚅了一句:“谢谢姐姐,我明天再来陪你。”
白曦的身影消失在吧台厚重的大门后,带走了那片区域最后一丝活人的气息。
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那句怯生生的:‘谢谢姐姐,我明天再来陪你。’
‘陪你。’
这个词,像幽灵一样,在空旷的酒吧里回荡。
凤九背靠着冰冷的金属酒架,整个人都隐没在黑暗里。
储藏室没有窗,隔绝了外面的景象。
她看不见白曦的离开,但她能想象出那个画面。
那个委屈的眼神,那个转身的背影。
她听到了,那句‘陪你’。
这个词比‘对我好’更具杀伤力。
它像一把柔软的刀子,剖开了她用冷漠和疏离伪装的层层外壳,触及到了那颗早已被她宣告死亡的心脏。
‘陪’。
不渝也说过。
在她因为家庭的冷漠而独自在异国过生日时,不渝抱着她,说:“以后每一年,我都陪你。”
然后,不渝她永远的失约了。
凤九缓缓地沿着酒架滑坐到地上,将脸深深地埋进双膝之间。
午夜色的真丝裙摆在冰冷的地面上铺陈开来,像一摊化不开的墨。
她的身体在极力压抑着颤抖。
她不是在难过,也不是在感动,而是在恐惧。
恐惧这种失控的感觉,恐惧这种被“陪伴”所承诺的、虚假的温暖。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所有的陪伴都有终点,所有的温暖都会冷却。
当一个人开始习惯陪伴,那么离别的那一天,就会比死亡本身更痛苦。
她不能允许任何人再“陪”她。
这场实验,从它被命名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独角戏。
她才是唯一的观察者和主导者。
可现在,那个被观察的“实验品”,却用最天真的方式,说要“陪”她这个观察员。
一切都乱了套。
她捂着脑袋,黑暗中亮起一盏老化的白炽灯,映出她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和那双空洞得如同黑洞般的眼睛。
“无聊。”
她轻声吐出这两个字,不知道是在说这场失控的实验,还是在说自己这可笑的反应。
“陪伴”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凌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