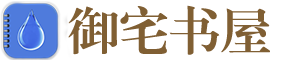渚园
作品:《白羽(H 强取豪夺)》 尾灯彻底融进夜色那刻,山庄门口只余风声。
沉翯在原地站了片刻,才收回视线。
王琦适时上前,躬身道:“沉总,今晚您是回去,还是在这边休息?”
沉翯微扬了扬头,“让人把我的车开过来。”
王琦随即应声去办,不多时,黑色的巴博斯停在台阶下,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
司机下了车,将钥匙递给王琦,王琦转呈给沉翯,又补了一句:“沉总,天色晚了,山路不好走,要不还是让司机送您回去吧。”
沉翯接过钥匙,指尖触感冰凉,“不必。” 他顿了顿,“我今晚回渚园。”
说完,拉开车门,兀自坐进驾驶位。
王琦站在车外,看着那辆黑色的车绝尘而去,心下诧异。小沉总自回国后,便极少回老宅,大多时候都住在市区的公寓,怎么今晚突然要回去?
车窗降下半寸,夜风灌进来,带着山林草木的湿冷气息。沉翯单手扶着方向盘,车辆在蜿蜒的山道上疾驰,车灯切开浓稠的夜色。
他确实极少回渚园。
那里承载的记忆,大多令他不快。
下午牌局开始前,沉峤给他挂来电话,以兄长式的命令口吻,让他今晚务必回家,陪父亲用晚餐。
他几乎是惯性地想要拒绝,话到嘴边,却在听见那句“妈今晚的航班到”后,生生拐了个弯。
所有推脱的借口都咽了回去,只淡淡回了句:“晚饭已经约了人,结束后,我会回去。”
沉峤比他大八岁,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沉北昆当作红乔集团唯一的继承人培养。沉翯记事时,沉峤已经跟在父亲身边,出入各种场合,学习如何周旋,如何算计,如何将权力与财富牢牢握在手中。
父兄的世界,沉翯从前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他们执迷于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偶尔回家,也总有各色客人来往。红乔的生意版图铺得极大,除了明面上的产业,灰色地带也涉猎颇深,三教九流,鱼龙混杂。
那些人,那些事,沉北昆和沉峤从不避讳他,只当他是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他们低估了孩童的记忆力,也低估了他的早慧。
青少年时期的沉翯,常常在路过二楼挑高的中庭回廊时,停下脚步,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楼下客厅里上演的一幕幕。
丑陋,肮脏。
沉翯厌恶这一切。他成长于一个金字塔顶端的特权家庭,享受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资源与便利,可内心深处,却生出一种近乎决绝的、想要将这一切付之一炬,将自己从这片肮脏的泥污中拖拽出来的渴望。
想到这儿,沉翯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方向盘下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
可现在呢?
他也在利用权力,试图将那个人捆绑在身边,让她不得不依附于他。
他对她,有着深入骨髓的欲念。无论是身体,还是其他。
五年前失去过她一次,他无法接受,她再一次彻底地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为此他可以不择手段,哪怕变成自己曾经最厌恶的那种人。
车灯刺破黑暗,前方,渚园的轮廓,在夜色中渐渐清晰起来。
轮毂碾过前庭碎石路面,最终在主宅门口停稳。
灯火通明,却照不散夜的浓稠。
沉翯熄了火,推门下车,脚步未停,径直走向主宅大门。
厚重的雕花木门前,管家陈伯已躬身候着,见他走近,立刻拉开门,恭谨道:“二少爷回来了。”
沉翯略一点头,越过他走进玄关,灯光煌煌,空气里有股木料与淡淡花香混合的气味。
他脱下外套,随手递给跟进来的佣人,抬眼便看见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沉峤。
长兄沉峤,身形比他略壮硕些,眉眼与沉北昆有七分像,继承了父亲的轮廓,却少了几分杀伐决断的狠戾,多了些世家子的浮华感。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领口微敞,正歪靠在沙发扶手上,手里捏着半杯威士忌,冰块碰撞杯壁,发出清凌凌的声响。看见沉翯进来,他坐直了些,却没起身。
“妈呢?”沉翯走到客厅中央,沉翯一边解着衬衫袖口的扣子,一边问。
沉峤下巴朝楼上书房的方向点了点,眼神往上瞟,“跟爸在里面谈事。”
他就这么靠着,端详着沉翯,眼神里却没有多少亲近的温度。
父亲让他下来等沉翯,尽一尽兄长的“本分”,他其实不大情愿。
他一直有点怵这个弟弟。
自从母亲沉昭华决绝地抛下一切远赴欧洲,沉翯骨子里某种东西,被彻底释放了出来。阴郁,寡言,情绪像被抽空,只剩下一个精致的壳。
思绪不受控制地飘远,沉峤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幕。
他大学毕业那年,正是年轻气盛、肆意妄为的时候,仗着父母都不在家,带了个水灵灵的小明星回家厮混。
两人在酒精和荷尔蒙的催化下,等不及回房,直接滚在了客厅的沙发上,衣服被扯得七零八落,那女孩儿皮肤白得晃眼,被他压在身下,正意乱情迷地娇喘。
情热时,女孩儿忽然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身体猛地一僵:“有、有人!”
沉峤不耐烦地回头,循着女孩儿惊恐的视线望去,正对上站在楼梯口,不知看了多久的沉翯。
那时他才十三岁,身量还没完全长开,穿着简单的T恤短裤,手里拿着一瓶刚从冰箱取出的的气泡水,玻璃瓶身上挂满细密的水珠,正沿着瓶身滑落,滴在地毯上,洇开一小块深色。
他眼睛黑沉沉的,像两口古井,就那么直勾勾、面无表情地盯着沙发上纠缠的两人。
平静得吓人,没有惊慌,没有好奇,也没有这个年纪男孩该有的羞赧。
还没等沉峤恼羞成怒地开口喝骂,少年先皱起了眉。
“记得清理干净,好脏。”
说完,他便转身,消失在楼梯转角。
从那以后,每当对上沉翯那双眼睛,沉峤总觉得不自在,好像自己的心思,连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欲望,都被剥得干干净净,无所遁形。
沉翯似乎并未察觉沉峤的走神,目光只在楼上书房紧闭的门上停留了一秒,便收了回来。
沉峤清了清嗓子,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随手搁在茶几上,“回来得正好,刚开的酒,要不要来一杯?”
沉翯的目光在沉峤手中的酒杯上扫过,眼神里辨不出情绪,“不用,谢谢。”
他绕过茶几,在距离沉峤最远的那张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自然地拉开距离。
啧,还嫌弃他。
不过正好,他也不大想和这个祖宗坐一块儿。沉峤心里暗忖,那点不自在又浮了上来。
他耸了耸肩,不再自讨没趣,转身又给自己倒了半杯,冰块在琥珀色的酒液里沉浮。他需要一点酒精来稀释这屋子里让人不舒服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