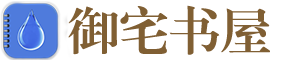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自从去年十月……你甩了我之后,没碰过任
作品:《踩过三个月亮后抵达春天》 车厢内,逼仄得如同一个临时搭建的、密不透风的审讯室。这个充斥着撕咬、掠夺,与其说是吻不如说是某种原始力量碰撞的交锋,硝烟弥漫在空气里。
奇怪的转折点,或许并不存在于理智层面。也许是唇齿间尝到的那一丝血腥气——不知是谁的,也许仅仅是牙齿磕破了唇内软肉——那微小的、锐利的痛感,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刺破了她因白予澈的背叛而麻木肿胀的神经。也许是那份近乎绝望的力度,让她在那一刻,荒谬地想起方才在诊疗室里,Dr. Chen 温和理性的分析,与眼前这头失控野兽形成的、令人晕眩的对比。虚伪的阳光与真实的黑暗,哪一个更伤人?
或者,什么都不是。仅仅是……累了。毁灭吧,就这样沉下去吧。她方才不就正走在这条路上吗?那扇泛着诱惑绿光的玻璃门,与此刻言溯离眼中燃烧的、不计后果的火焰,本质上,或许是同一回事——都是通往遗忘与沉沦的捷径。
与其去触碰那些可能带来短暂虚假快乐却后患无穷的禁忌药物,不如……就在这片早已泥泞不堪的旧战场上,再滚上一遭。反正,还能失去什么呢?
人在绝境中寻求慰藉时,有时并不选择光明,反而会扑向更深的黑暗,只因那黑暗的轮廓如此熟悉,熟悉到令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挣扎的力道,不知何时,悄然卸去,身体变得柔软。抗拒渐渐消弭,不是接受,更像是某种被耗尽后的、带着自毁倾向的默许。言溯离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细微的变化,如同一滴投入滚油的冷水,瞬间在他体内引发了更剧烈的爆炸。像确认战利品的野兽,吻的力道未减,却多了几分急切和难以置信的狂热。
深灰色的连衣裙被粗暴地撩至腰间,昂贵的面料褶皱不堪,像她此刻混乱的心绪。裙摆被他粗暴地撩至腰际,露出底下象牙白的内裤,边缘已被不知何时渗出的湿意洇染出深色。空间太过狭小,言溯离几乎是将她半抱半按在自己腿上,让她背靠着冰冷的、还残留着她方才挣扎时体温的车窗。他解开自己皮带的金属扣,发出沉闷而刺耳的“咔哒”声,像是某种仪式启动的信号。拉链被猛地拽下。
没有前戏,没有安抚,只有最直接、最赤裸的入侵。他硬挺的欲望带着某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撞碎了最后一层名为“界限”的薄冰。程汐背靠着冰凉的车门,承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带着痛楚的贯穿。她死死咬住下唇,将一声可能溢出的痛呼硬生生咽了回去,只有细密的汗珠从额角渗出,洇湿了鬓发。
“程汐……”他低吼出她的名字,声音嘶哑得厉害,像是在确认,又像是在祈祷。
这一刻,言溯离的大脑同样混乱不堪。
“二级。旁系。血亲。”
他知道,他此刻正在做的事情,是跨越人伦的深渊,是万劫不复的沉沦。可怀里这个女人,她的柔软,她的气息,她此刻因为紧张和恼怒而微微颤抖的睫毛……这一切的诱惑,让理智的堤坝崩塌,奔涌而出的是人性中最原始、最不计后果的洪流。
车窗外,惨白的街灯均匀地洒下,照亮了这方寸间的混乱。汗水,喘息,皮肤与皮革摩擦的黏腻声响,以及某种近乎绝望的、原始的搏斗……一切都扭曲、变形,像一场发生在密闭容器里的、无人观看的困兽之斗。
他觉得自己像个疯子,一半灵魂在尖叫着抗拒这禁忌的触碰,另一半却被那源自血脉深处的强烈吸引力和积压了近一年的疯狂思念所驱动,只想将她彻底揉碎,吞入腹中,永远占有。
上帝若有悲悯,此刻或许会轻轻阖上眼。人类的情感迷宫,有时竟会通往如此荒芜、怪诞的死胡同。而他,那执着于占有、却被血缘诅咒缠身的男人,正试图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名为禁忌的墙壁上,凿开一个通往救赎或更深地狱的缺口。
然后——
一切戛然而止。
突兀得像一根绷到极致的琴弦,毫无预兆地,“嘣”地一声断裂。
言溯离的身体猛地一僵,紧接着是一声短促而压抑的、混合着错愕与难以置信的吸气声。那股横冲直撞的力道瞬间失控,只剩下僵硬的、滚烫的身体还停留在她体内,却已释放了所有勃发的生命力。
时间仿佛凝固了。
只有他粗重不匀的喘息,和她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无限放大。
言溯离僵的身体还维持着入侵的姿态,大脑却一片空白,只剩下一种被当头泼了一盆冰水的狼狈和……难以置信的羞耻。他,言溯离,竟然……秒射了?在她面前?
静。死一般的静。
程汐愣住了。大脑因缺氧和方才的激烈而一片空白,身体还残留着被侵入的钝痛和不适。她甚至需要几秒钟,才迟钝地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就这么……结束了?
一股难以言喻的、极其荒谬的情绪,如同潮水般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她肩膀微微耸动,眼角甚至笑出了生理性的泪花。她抬手捂住嘴,试图抑制,却徒劳无功。那笑声在密闭的车厢里回荡,驱散了刚才那令人窒息的紧张和屈辱,带来一种……荒诞到极致的轻松感。
程汐在笑。是真的在笑。
这不是嘲讽,甚至算不上幸灾乐祸,这是一种纯粹的、近乎癫狂的、在极致压抑和荒诞后爆发出的——开心。是的,开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这滑稽的、狼狈的收场,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那浓得化不开的绝望、愤怒与自我厌恶。
言溯离先是僵硬地愣在原地,被她突如其来的、如此纯粹的笑声搞得措手不及。他脸上瞬间闪过羞恼、难堪,他甚至想粗暴地捂住她的嘴,或者用更激烈的方式来夺回主导权。
言溯离猛地退出来,动作间带着几分恼羞成怒的狼狈,手忙脚乱地试图整理自己凌乱的衣物。这简直是他人生中最丢脸的时刻,比任何商业谈判的失败、任何对手的挑衅都更让他无地自容。
“好笑吗?”他咬着牙,声音从齿缝里挤出来,带着最后一丝可贵的自尊。
程汐终于稍稍止住了笑,但眼底的笑意仍未褪去。她侧过头,看着他那副窘迫又强装镇定的样子,摇了摇头,声音里还带着笑过后的轻快:“没,我就是……没想到。”
她确实没想到。没想到一场充斥着暴力、胁迫、愤怒和绝望的对抗,会以这样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收场。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像是一出蹩脚的荒诞剧,冲淡了她心头积郁的沉重和苦涩,让她在这一片狼藉中,意外地感到了一丝……轻松。
言溯离看着她眼中那真切的笑意,心头那股烧灼的羞耻感竟奇迹般地消退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尴尬,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她笑了。不是哭,不是冷漠,不是厌恶。她在笑。这比什么都好。
他清了清嗓子,神色反而坦然了些,甚至带着点自嘲的意味,直视着她的眼睛解释道,“一年了。”他开口,声音因为刚才的激烈而显得有些嘶哑,却异常坦然,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意的强调,“自从去年十月……你甩了我之后,没碰过任何人。”他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像是在陈述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也像是在不动声色地为自己辩解,“身体太久没……嗯,反应快点,很正常。”
他刻意强调“没碰过任何人”,像是在为自己辩解,更像是在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她表露某种扭曲的“忠诚”。像一个经验老道的赌徒,在输掉一局后,不动声色地整理好筹码,评估着下一轮的牌局。
他没有提那些更深层、更汹涌的惊涛骇浪,那些关于后怕、关于绝望的潜意识恐慌——脑子里那根关于“血缘”的弦绷得太紧,身体已经先于意志做出了逃离“罪恶现场”的反应。
“是吗?”程汐挑了挑眉,拉下被撩起的裙摆,动作从容地整理着凌乱的衣襟,仿佛刚才那场突兀的情事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意外。“言总定力惊人。”语气里听不出是信了还是在讽刺。
言溯离看着她重新恢复了那种淡漠疏离的样子,内心奇异地安定了下来。笑吧,至少她笑了。比刚才在店门口那副了无生气的样子,或者在车里激烈反抗的样子,要好太多了。
至少,这一刻,她看起来,不像是要去毁灭自己了。这就够了。
这算什么?一次未遂的报复?一场荒腔走板的闹剧?还是一次……没有预谋的、极其不完整的出轨?
无论如何,车厢里的空气,似乎悄然改变了。那股剑拔弩张的紧张感暂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古怪、更加难以定义、混合着尴尬、疲惫和一丝微妙变化的……微妙氛围。
命运的齿轮,就在这样荒诞不经的瞬间,悄然啮合,转向一个无人能够预料的方向——这当然不是结局,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开始。但对此刻的两人而言,这已经是命运所能给予的,最不坏的一种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