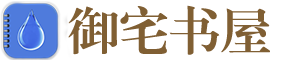三十五、春雨
作品:《淫乱血脉(中世纪,nph)》 战斗在晨雾中结束,血在石砖上晕出一片片深色的潮痕。那些喊杀、崩溃、咒骂的声音,像被时间一口气关进了瓶里,封死。
我没有亲手埋葬叶菲米,但我为他选了位置。
他被安葬在延苏家的家族墓地里。那片老林背阴、沉静,也是我祖母,父亲,还有忤逆的叔叔们的葬所。
叶菲米原本不属于那里。可我把他葬了进去,像是把一场太久不肯醒的梦塞回历史里,让它终于沉底。
他的墓碑极小,不刻称号,不列功绩,只刻了一个名字,和生卒的年数。我亲自定的石刻。
那天风很冷,云压得很低。我站在坟前,什么都没说,像站在自己埋下的一段骨头前,试图忘记那段骨头曾属于身体。
我放过了他家所有人。
他的小侄女依然在修道院里念书,他母亲早年去世,他堂兄弟在战后纷纷上书请求赦免。
我全都准了。
可我也把宫廷里所有与他有关的人——他的幕僚、骑士、密探、书吏,全数遣散,驱逐出伯尔拉德。他们不是叛徒,他们只是他的人。
在王座上,我不能再留他的人。
他的妻子,维奥莱塔,在城破之前战死了。
那桩婚姻,是他父亲临终前给他安排的最后一场交易。
他们成婚的时候,叶菲米在我身边笑得无比自然。我还记得婚礼那夜,他喝了半壶蜂酒,唱起小时候学的民谣,拍着我的肩,说:“她是好人,我不亏。”
她是好人。
她也确实不亏。
只可惜她为这桩婚姻付出了生命。
她死在王宫北门。他们没有孩子,最后什么也没留下。
我将她的尸骨葬于西城墙下的贵族墓地,不列其名,只用家徽为志。
战后的日子宁静得像不曾发生过流血。我重组了枢密院,立起了新的边防法案,整顿了财政,把特兰西瓦尼亚收为王领,遣使前往神罗重申誓约。
我的王国看上去,比从前更坚固了。
可有时候夜里我会在梦中醒来,以为自己还在那个火盆焦灼的帐篷中,睁眼就能看见他坐在床边、唇色苍白、手指冰凉。
我想问他:“你醒了吗?”
却只有空风回应我。
我后来问萨维尔开提,你当时不是要去救他吗?为什么又什么都没做。
萨维尔开提说:“我知道我救不成他,就像他当时救不了我一样。”
我愠怒道:“我当时又没把你怎么样。”
萨维尔开提眼珠一转,缓缓开口:“活在爱丽丝臂弯里的萨维尔开提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一个女巫。”
“就像如果他当时跪下了,活下来的就是另一个叶菲米了。”
德米特里替代了骑士团里叶菲米的位置,其实他早就是一个优秀的骑士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
我一直活在那个新婚之夜带上头盔去找叶菲米比试的夜晚,直到现在我才肯往前走一步。
我常常想,叶菲米到底是什么。
是朋友?是敌人?是爱人?是共治者?还是我自己的一块镜子?
我以前以为他是朋友,然后是爱人,最后变成了敌人,然后又变回朋友。
我走出门,外面是春天的第一道春风。
“叶菲米之于我,如人生的第一场春雨。”
这场春雨下了太久,我原以为这些乍暖还寒的日子是痛苦的磨难。
但我没意识到我其实躲过了太多场严冬。
我人生的最后一个春天来的很晚,雪水还未全融,风从东边山岭吹来,带着落叶的声响。
我躺在床上,身上的骨头像一场很久以前的战争——它们没有打完,但都已经疲惫。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发呆,一呼一吸,像是费尽全力。
这时候门开了。
他走进来,叶菲米——不是他,是我的二儿子。那张脸和他年轻时并不像,只是眉眼间偶尔有那么一瞬会让我恍惚。
他怀里抱着他刚出生的小女儿,那孩子才几天,皱巴巴的,脸红得像被热水泡过的花蕾。
“她叫什么?”我问。
他轻声说:“爱丽丝。”
我点点头。嘴唇很干,想笑一下,结果没成功。
他把孩子递给我。我用枯瘦的手指轻轻摸她的额头。她睁开眼,看了我一会,又闭上。
那一瞬间,我忽然感到有什么被点亮了。像我这一生曾经抓住过的每一缕光,都在这个婴儿眼里闪了一下,然后全都退回了黑暗里。
我脑子里忽然很清晰。我看见叶菲米——那个叶菲米,穿着旧军服站在帐篷口,朝我笑。他的头发被夜风吹乱,眼睛一如既往地清澈。
我看见萨维尔开提坐在青石柱边,仰头喝酒,红裙子铺了一地,说:“你怎么还是没学会不爱他呢?”
我看见父亲、母亲、我新婚夜窗外下的雨、还有那些我在王座上一个个推倒的人。
他们都站在我面前,又一个一个地退开。
我没有再说话。只是把那孩子的手握在掌心,慢慢合上眼。
不是睡去,是放下。
“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重逢。”萨维尔开提放下手上的一束花。
她站在墓前,看着国王伊利克的墓碑旁小小的,只有名字和生卒年的石碑,这样说道。